死水微澜电视剧(死水微澜电视剧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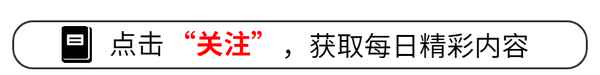
文丨朝史暮今
编辑丨朝史暮今
该处细节的点染,不但烘托出蔡大嫂内心痛苦的挣扎,而且让罗邓二人的超越道德之恋在世俗的鄙薄声中愈加坚决,使二人的情感具有了反抗世俗的动人力量。
又如,让罗邓二人在劳燕分飞之前逛宝光寺、求送子观音等,诸如此类细节添加,在电视剧《死水微澜》中比比皆是,使蔡大嫂与罗德生逾越道德之恋不仅情有可原且让人感动。二是强化原著中的情感细节,使情感发展脉络清晰化。
原著中蔡大嫂对罗德生的最初动情,仅由刘三金的一句话转述:“她向我说得很清楚,自从嫁给蔡傻子起,她就爱上了你,只怪你麻麻胡胡地”。
围绕这一句话,电视剧《死水微澜》补叙了这样的细节:在邓幺姑嫁给蔡兴顺的当天,幺姑透过红色的喜帘,看着头戴红花的罗德生,以为新郎是罗德生,无限窃喜。当她知道新郎是蔡傻子时,她的情感由暗自窃喜变为心灰意冷。
这一转变,不仅烘托出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和故事的戏剧性,也使罗德生与蔡大嫂的情感发展更加合乎情理。
电视剧第六集,专以“刘三金穿针引线”为剧集名表现罗邓二人的情感在“将说不说”时的压抑与试探。当二人被刘三金“点拨”之后,增加了这样一个细节:罗德生站在蔡大嫂的门外。蔡大嫂开门。
蔡:“你……”,罗:我……,下雨,没有事出来走走。两人尴尬相视。当二人情感说破时,又增加了很多细节性的场面,表现二人情感的真挚热烈。这些原著中并未详述的情感细节的添加使罗邓二人的感情显得格外细腻。
三是加入原著中没有的人物形象。“玉儿”这一原著中莫须有的人物充当了类似的戏剧作用,通过玉儿对罗德生纠缠,强化了罗德生对蔡大嫂的情感忠贞。
以上小说《死水微澜》改编为电视剧以后的细节添加,使电视剧《死水微澜》有更加充裕的时间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以完善人物形象的塑造。正如有论者所言,“(电视剧)它可以将时间的优势转化为对细节的刻画,从而成功地达到对人物内心的描写”。
删减。从叙事所占用的篇幅和所耗费的阅读时间而言,电视剧对川西坝的民风民俗民情描述不及小说所占用的时间。
在小说中,如“在天回镇”和“交流”部分,叙事者对天回镇的地理位置,天回镇的铺子,天回镇的赶场,大市,小市,声、色、远、近,总写,特写,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铺陈描述。
电视剧《死水微澜》则在开头以全景镜头鸟瞰天回镇,并配以叙事人的话外音,对集市上的商品给以特写,耗时约一分钟,将作者的数千言囊括入镜头之中。
正如有一位电影理论家说过“一个画面抵得上千言万语”,电视剧《死水微澜》叙事对小说中天回镇的民俗、生活等的转换与呈现,显得更为简洁。另外,从内容而言,电视剧改编之删减法运用最为明显之处是对小说中“序幕”一章的删除。
小说序幕部分,由“我”的儿童视角回忆“我”儿时读书的记忆、坟园经历,以及“我”与蔡大嫂的初遇。
序幕之后的第二部分到第六部分,以倒叙的手法回忆出蔡大嫂“一生三嫁”的经过。电视剧叙事则直接以“幺姑闹嫁”为始,以“掌柜娘变成了顾三奶奶”为终,按“线性时间顺序”进行叙事。
改动。严格地说,删减、增加也属于改动,但此处的“改动”并不是指删减或添加,而是指导演或编剧在细节上刻意追求的变化。通过这样的改动,改编文本与原著之间在某些细节上往往出现一些富于意味的变化。
这样的改动包括“张冠李戴”的置换,如小说中余树南“掉包”救人的英雄事迹转移到罗德生身上,使罗德生作为袍哥老大的沉着、冷静的特征得以体现。
还包括在细节上一些饶有意味的改动。如小说中陆茂林送蔡大嫂玉魌刀插针这一细节与电视剧对这一细节的处理是不同的。小说中的蔡大嫂不仅收下了陆茂林送的玉魌刀插针,而且拿脸颊轻轻地挨了一下陆。
而电视剧中的蔡大嫂,不仅没有收下陆茂林送的玉魌刀插针,还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情意。又如,电视剧以“蔡大嫂在喜轿中潸然落泪,蔡兴顺蹒跚而来”结尾,小说则以顾三奶奶高喊“只要我顾三奶奶有钱,一肥遮百丑”结尾。
类似于这样的增删、改动,笔者将在下文的论述中多次提到。正如改编理论研究者布鲁斯东所说,当选择不同的媒介进行故事讲述的那一分钟前,变化与差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死水微澜》从采用电视剧这一媒介进行讲述时,就意味着会以与文字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影视屏幕上,实现从让读者“看见”到让观众“看见”的转变,种种增添、删减,改动就在所难免。
小说《死水微澜》中洋洋洒洒数千言关于天回镇地理位置,风俗人情的描述,在电视剧《死水微澜》的叙述中转化为鸟瞰的俯拍镜头;不甚鲜明的故事情节发展脉络在电视剧叙事中被清晰化……种种变化,表现着两种不同的叙事媒介在叙事时两种不同的“看见”方式。
电影艺术家D.W.格里菲斯在1913年总结自己的主要创作意图时说:“我试图要达到的目的,首先是让你们看见”,英国小说家康拉德在小说《黑水手》序言中说“我试图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文字的力量,让你们听见,让你们感觉到,而首先,是让你们看见。”
这两种关于“看见”的言述,隐隐透露出了关于两种“看见”方式的区别。正如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所认为的,小说与电影在起源、受众、素材、表现手法、生产方式等各方面都存在天然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从一种“看见”转为另一种“看见”时,必须有所变动,因此,电影艺术家所改编的只是小说的一个故事梗概。
英国电影理论家克莱·派克,也表达过相类似的观点,“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绝不是原始资料的一种机械复本,而是一套表现世界的成规转化和变换成另一套”。
在这样一种共识之下,去考察《死水微澜》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探寻诸如上文所提到的增、删、改动背后隐藏着的电视剧叙事与小说叙事的种种差异。
总体而言,小说《死水微澜》中的叙事方法更为多元,倒叙、顺叙、插叙,补叙等叙事手法交叉出现在小说《死水微澜》中,而电视剧《死水微澜》的叙事则体现为较单一的线性叙事。
如小说第一部分“序幕”先交待了蔡大嫂与第三个男人顾天成婚后的生活状况,第二部分“在天回镇”到第六部分“余波”,再回溯出蔡大嫂“一生三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的缘由。
在叙事过程中,叙述者同样习惯于先交待事情的结果,再叙述故事的经过。如“在天回镇”一部分,小说的叙事时间直接进入蔡傻子与邓幺姑“新婚以后”,然后再倒叙蔡大嫂少女时代对成都的向往,以及嫁给了蔡傻子的经过。
“余波”部分,叙述者也以一种先知者的声音暗示了故事的发展趋势:“大概是物极必反罢,罗歪嘴的语谶,大家的希望,果于这一天实现了”,然后再交代了罗邓二人的分离。
相较于小说中的叙事时间,电视剧《死水微澜》的叙事则是按照“事件本身的有次序的时间”进行讲述的。
电视剧《死水微澜》省略掉“序幕”一部分,以幺姑闹嫁为始,以“蔡大嫂变成顾三奶奶”为终,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了幺姑从待嫁到出嫁再到改嫁的传奇经历。
正如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所认为的,小说中对事件的讲述本能地打破自然时序,这是“古已有之”。
而电视剧作为一种家庭艺术,它主要通过电视机或录像机在开放的家庭环境中进行播放,观看者易受旁物影响,因此它倾向于以一种生活流的方式进行讲述,并依靠绵延的故事来吸引观众。
正如尹鸿所认为的,“电视剧在结构上一般并不采用套层结构等等复杂的叙述方式,而是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线性结构,像生活本身一样慢慢流动。”因此,电视剧删掉了小说中的“序幕”部分。还值得一说的是,对“序幕”部分的删除所透露出的改编者的意图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其一,从故事的完整性来看,删掉“序幕”不会影响观众对故事的理解。同样,如前所述,电视剧讲述故事的方式呈现出生活流的特点,而从“序幕”部分到故事主体部分的过渡中所包含的复杂叙事时空的转换,也不利于电视剧的生活流叙事。
其二,从“序幕”的具体内容看,其中所塑造的蔡大嫂的形象与电视剧《死水微澜》企图完善的痴情而仗义的经典言情剧女主角形象有不和谐之处。
“序幕”部分蔡大嫂的出场交代了她嫁给顾天成以后的生活状态。不管是她的外貌、言行还是穿着打扮、待人接物,所流露出的都是一种积极的、热爱生活的态度,单对她“笑”的描写作者就花了不少笔墨。
于作者李劼人而言,经历了惨痛的婚姻变故之后的蔡大嫂仍“笑”对生活的态度,正好表现了一种来自民间的原始生命力。
而于电视剧的改编者而言,电视剧中蔡大嫂最后满腹委屈、无比哀怨地被迫易嫁顾天成的结局与“序幕”中所呈现的蔡大嫂知足的生活状态在情理上有抵触之处。
因此,这也是电视剧《死水微澜》省略掉小说第一部分“序幕”,而以邓幺姑“望成都”为故事起点的原因之一。
从文字到画面的转换过程,其中的差异也明显地体现在对川西坝民风、民俗、民情的表述上。小说第三部分“交流”中描写“天回镇赶场的日子”,作者以全知全能视点,记述了大市、小市、货品、赶场的人,洋洋洒洒几千字。
诸如此类对川西坝民风民情民俗的描写,小说中俯拾皆是:如对东大街的新年花灯、赶青羊宫、婚丧嫁取等风俗礼仪的描述。
参考文献:
- 陈犀禾.《电影改编理论问题》[M]上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
- 严福昌 《川剧艺术引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