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女厕所门上的字
1995年,30岁的张越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半边天》的节目主持人。
那时候的她留着短发,身型圆润,总是喜欢穿着宽松随意的衣服。
她很特别。端庄、温柔、知性,台里的女主播换了一批又一批,而她的形象一直是犀利、直接,甚至还有些尖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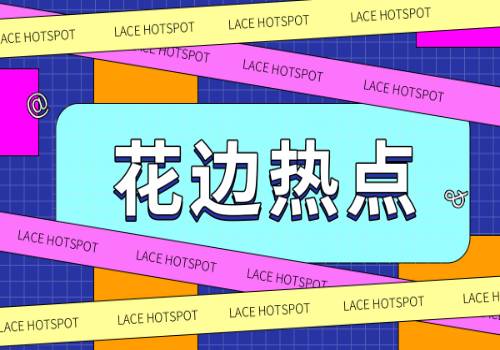 (资料图)
(资料图)
张越的主持生涯里有许多高光时刻。
一个反复被提起的例子是,在韩红因外形遭受诸多非议和恶评时,是她主动邀请韩红到央视做客,给予了韩红走入主流媒体的机会。
可张越本人对这些所谓的“名人效应”并不在意,相反的,她更想诉说的,其实是平凡日子里的平凡人生。
张越的主持生涯也有很多灰暗故事。
比如在她刚刚主持《半边天》时,就曾因外貌与身材遭到攻击,有观众写信给央视质问台长:“张越是不是你家亲戚?为什么找她当主持人?其他人都死光了吗?”
多年来,张越探讨着偏见与女性的关系,也一度活在“偏见”里。
她从不为此担忧,她足够个性和强大,这是她与《半边天》与生俱来的缘分。
将时间拨回到张越入职央视的前一年,1994年,联合国决定于次年在北京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即将退休的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寿沅君,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决定背后的东西,一个“史无前例”的想法开始在其脑海中构思。
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央视为许多人群创办过专门节目,唯独忽视了女性群体,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寿沅君联合其他两位编导一同起草了一份女性节目策划书,并将其递交到台里,审核很快通过了,《半边天》诞生了。
央视《半边天》节目片头
《半边天》初现雏形的这一年,张越29岁。
198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她一直在某中专院校当语文老师。学校主攻金融类学科,语文成了课表里最不重要的存在,生活很清闲,课余时间也可以发展一些副业。
大学毕业后,张越的许多同学都进了电视台,某天一位在央视实习的同学找到她,说台里现在急需两个小品剧本,想请她帮忙写一下,闲着也是闲着,她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编剧生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英达留学归来,正式将“情景喜剧”的理念引入国内电视行业。
1993年前后,英达执导的《我爱我家》开播,广受好评。观众的呼声不断,制作方也欣喜万分,于是马上通知剧组,要在原有的剧本基础上再加80集的篇幅。
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海报
当时《我爱我家》的总编剧是梁左,得知这一消息后哭笑不得。情景喜剧边写边拍的高压模式本来就让他崩溃,如今要再加80集,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帮梁左分担压力,英达找到了张越,彼时他听说,这位女编剧写剧本的速度奇快,而且笔下的段子和包袱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在认识英达之前,张越根本不懂什么是情景喜剧,这个东西她没写过,也不会写。英达倒不在乎,哈哈一笑,告诉她:“反正谁都不会写,全中国也没编剧写过,试试呗。”
英达说得坦诚,张越也不好拒绝。她问导演要了几期已完稿的剧本,回家看了看,乐得“笑出了猪声”。
兴致来了,她当晚就写出了2集,其中有一集便叫《真真假假》,讲的是傅明老爷子(文兴宇饰)假装生病为引起全家注意,结果反被误诊为癌症的故事。
《我爱我家》片头截图
编剧:张越、梁左
在《我爱我家》的后80集中,张越参与编写了近20集内容,王志文和江珊也曾客串演出过她编剧的章节。
江珊客串演出《我爱我家》(1993)
王志文客串演出《我爱我家》(1993)
《半边天》正式播出后,央视推出了一系列以女性群体为主视角的栏目,这当中有一档节目名为《好梦成真》,节目内容就是用24小时的时间,帮一位女性完成心中的梦想。
那个时候张越是这档节目的策划之一,过程中她发现,节目组拍过的女孩梦想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种:歌星、模特和空姐。
闲聊时她跟编导说:“这有什么意思?如果是我,我就梦想当个厨子。”
一句无心之言,又把张越从幕后送到了台前,她没想到,过了几天节目组竟真的把她送到了苏州松鹤楼,体验了一把当厨子的感觉。
在苏州体验厨师生活的张越和大厨师父
这期节目播出后,意外收获了不错的收视率,而张越面对镜头丝毫不胆怯、能说会道的表现也引起了《半边天》制片人的注意。
此后,《半边天》接连三次邀请张越做对谈嘉宾,直到第四次见面,制片人才告诉她,其实节目组一直想找一位可以主持脱口秀栏目的人,但台里的女主播更习惯传统主持模式。节目组想让张越试试,又担心观众无法适应,毕竟在此之前,央视舞台上的女主持大多为倪萍、杨澜这样的知性形象。
所幸,观众的反响还不错,张越入职央视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是1995年,30岁的张越坐进了《半边天》的演播厅,彼时的她只觉得“这事挺好玩”,全然不知道命运的转折也就此开始了。
张越早期入职央视的样子
作为亲身参与者,张越是最早发现《半边天》与其他节目有本质不同的人。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它是当时央视唯一一个以性别定位的节目,还展现在许多细节上。
在《半边天》工作的每一位成员,在正式上岗前都要进行性别培训课,许多编导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才了解到,原来性别也分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
简单讲来,生理性别是二元的,只有男、女之分;可社会性别是多元的,指作为一个男性或女性的社会含义,泛指社会对男女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
在《半边天》刚刚开播的那几年,许多话题都是围绕“社会性别”展开的,例如“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构成是否合理?如何消除“男强女弱”的刻板印象?“养儿防老”背后的性别歧视……
这些话题时至今日仍在被讨论着,而这也是张越心中《半边天》的成功之处:
节目探讨的不仅仅是时下热点的话题,更是一代人的思考与困顿。
《半边天》节目截图
对于女性相关的话题,张越和《半边天》都是敏锐的。那时候有一则女士内衣的广告上写着“挺起胸才能抬起头”,言外之意,大胸值得骄傲,胸小很不体面。
张越和编导看到后火冒三丈,立刻就制作了一期节目,主题便是探讨社会对于女性的某些期待是非常冒犯且带有歧视的。
最初进入《半边天》的日子,张越对这份工作带有无限的热情。
节目在深夜播出,而她的工作内容,便是坐在演播厅里与多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探讨一些时下敏感的话题。
上到女性在历史中的角色扮演,下到女性在日常生活里的衣食住行,张越每一次都奔着“干倒男嘉宾”的目标使劲儿,一度以为在辩论中取得胜利,便是女性的胜利。
可渐渐地,张越感到了疲惫与无奈。
每天坐在演播室里高谈阔论有用吗?在节目中,她可以以一个女主持人的身份用嘴“打败”在场的男嘉宾,可节目结束后呢?那些实实在在生活在普通日子里的女性,是否会因为自己的一次谈话,而获得尊重和理解呢?
内心的疑问和纠结越多,张越对于《半边天》的归属感就越来越少。节目的宗旨是“倾听女性表达”,可坐在密不透风的演播室里,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了。
1997年,张越决定从央视辞职。她找到了领导,说出了内心的顾虑。领导反问:你觉得的“女性声音”应该如何表现?
张越默不作声,因为她也不知道答案。僵持中,领导拒绝了她的辞职申请,让她回去再想想,而张越这一想,就是整整两年。
不需要主持的日子,张越再次回到幕后做起了策划,时常会跟着节目组出差采风。
一次,她与同事一同到深圳罗湖火车站录节目。在火车站的女厕所里,她发现蹲坑的木门上写着许多字。她本以为会是一些有关住宿、租房,或者色情服务的信息,但走近一看,大吃一惊。
“深圳我爱你,你给了我梦想;深圳我恨你,你夺去了我的灵魂。”
在那些肮脏破旧的木门上,张越看到了无数“深漂”女性内心的挣扎和无奈,那些都是她们平常无法诉说,却又渴望被听见的心情。
“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张越斩钉截铁。
从深圳回到北京后,张越再次回到了《半边天》,并提出了走出演播厅,与女性面对面交流的节目改版要求。对此,领导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在深圳火车站女厕里写字的可以是任何一位女性,那后续节目的具体选题该如何确定?
张越回答:有故事、有经历,通过她能够清晰看见时代和群体的人。
带着一个并不具体的形象,张越和节目组开始了“寻人”之旅。
她曾采访过一位姓杨的女性。结婚前,小杨是一位叛逆少女。初中毕业后,她自愿放弃了重点高中的录取名额,跑到社会上打零工,几年后,通过自学她又考上了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
24岁那年,在父母的催促下,她与一个男孩闪婚,不久之后,二人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此后,她听从婆婆的意见,辞去了原本高薪的设计师工作,在家做起了全职妈妈。
女儿上小学后,她有了回归职场的想法,可在婆婆眼里,这是小杨有“外心”的表现,说什么也不同意儿媳外出工作。几番争执无果,小杨选择了离婚,除了女儿的抚养权,她什么都没要: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我不需要。我可以再挣,我不在乎。”
《半边天》节目截图
与小杨形成对比的,是一位来自贵阳的大姐,名叫丽丽。在40岁之前,她近乎完全丧失了人生的掌控权。
出生于60年代的偏僻农村,丽丽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最多的事,就是忍受饥饿和贫穷。小的时候,一家五口挤在月租5元的草房里,16岁之前丽丽甚至不知道睡在床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成年后,丽丽到贵阳打工,因为没有钱租房,她在老乡家里的猪圈中睡了一年。经工友介绍,她认识了后来的老公,对方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曾因诈骗被劳教处罚。男人告诉丽丽,结婚之后便可以让她吃饱饭、穿好衣、住楼房,于是为了生存,她结婚了。
婚后,男人嗜赌成性,每次输钱都会对丽丽拳打脚踢。恐惧和伤痛成了婚姻里的噩梦,将近10年,丽丽只能依靠安眠药入睡。
改革开放之后,丽丽经营起一间饭馆,生意越来越好,小饭店变成大酒楼,丽丽逃离了贫穷,却没能离开暴力的丈夫。
根据丽丽回忆,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曾向自己提出过上百次离婚,每一次都是要一笔“赔偿金”,拿到钱就反悔。终于有一天,男人又一次开出条件:一次性拿出35万,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丽丽有些意外,问这次是真的吗?对方给出了无比肯定的回答,理由是:一位算命的说丽丽“八字太硬”,二人如果继续在一起,男人一辈子都别想发财。
这样的理由让张越哭笑不得,她问丽丽,为什么明明那么痛苦,却还只是被动地等待丈夫离婚,而不是主动主张权利?
丽丽回答:“我怕他会杀了我。”想了想,她又说:“所以说女人可怜啊。”
《半边天》节目截图
一个人出生、成长的环境决定了其眼界与三观,于是圈子形成了,差异也随之产生。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张越采访的女性中,提到“爱情”,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女人会聊到琼瑶电视剧、亦舒小说对自己的影响;可农村女性更多看重的是“找个人过日子”。
在都市女性的眼中,新时代的两性关系更注重自由与个性的表达;可对远在农村的妇女来讲,“爱情”也许只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生存远比浪漫重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不同条件下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产生后又如何解决?
张越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要做《半边天》,这些故事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到,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
张越主持《半边天》节目截图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波澜壮阔。
张越说,主持《半边天》以来,这是她最真实的感受。
早些年想要找到一些愿意表达自己的女性,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为了倾听她们,张越和节目组时常需要扛着摄像机全国各地跑。
见到的人越多,张越便更能清楚地感觉到,外界给予一个人的所谓期待与标准,往往与其内心真实的想法和现实人生大相径庭。
张越采访现场
张越曾采访过一位姓胡的女士,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近乎“无可挑剔”。胡女士在供电局工作,丈夫是她的同事,二人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收入可观。结婚后不久,他们成功分到了房子,不久之后又生下了儿子。
在外人看来,胡女士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可见面后张越才知道,原来胡女士的丈夫沉迷炒股许久,近乎赔掉了家中所有积蓄,日常工作或者股市不顺,他便会对胡女士拳脚相加。
过去几年,胡女士几次想过离开,但每次见到丈夫诚恳地道歉,她都会心软、选择忍耐。直到有一次,她亲眼目睹了丈夫将年幼的儿子打得浑身是伤,而理由仅仅是写错了两个英语单词,她终于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
“过去以为每个家庭都一样,有了问题就想着‘生个孩子就好了’,可现实并不是这样的。”胡女士告诉张越。
《半边天》节目截图
“婚姻就是‘真心话’与‘大冒险’的结合体。”张越说,过去讲起女性与婚姻的关系,大家都习惯用“幸福”和“不幸福”去衡量和定义,但走近了才发现,一切远比想象的复杂。
《半边天》还有一期节目叫“花甲新娘”,讲的是一对“老少恋”,女方比男方大32岁。
节目组扛着设备找到二人居住的村子里,问当地村民如何看待这对夫妻,不出意外的,大多数人的评价都绕不开“不正经”。
在后续的采访中,节目组得知,因为这段“忘年恋”,夫妻二人已与全家人断绝关系,为了能够和26岁丈夫“在外貌上匹配”,已经58岁的妻子还去整形医院做了全脸除皱手术。
《半边天:花甲新娘》主人公(2009)
由于一直遭受排挤和非议,他们搬到了远离村庄的地方,常年住在自建的窝棚里。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他们的爱情“不会有好结果”,唯独他们坚信“只要俩人在一起,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生活就能幸福。”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这对相差32岁的爱人仍然相守。短视频时代来临后,二人开始尝试在网上发布一些日常视频,凭此还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查看评论,议论仍在继续。
十几年过去了,人们还在为此争论,他们真的幸福吗?答案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半边天:花甲新娘》主人公(2022)
刚开始做节目时,张越很喜欢争论,对与错,是与非,大家摆在明面上说得清清楚楚。
可当她真的走进故事,走近那些主人公,她渐渐发现,相比“说”更重要的是“听”。
《半边天》中出现的每一位女性,都不应该被看做是节目输出观点的工具,而应该是被看见和了解的,有血有肉的美丽个体。
而再看看如今一些综艺、选秀节目的营养价值……一声长叹。
《半边天》节目截图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各行各业都迎来了巨大的转折,同时迈上新台阶的还有《半边天》。互联网飞速发展,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快速增多,表达欲也愈发旺盛。
在那几年间,张越的电子邮箱每天都会塞满全国各地观众的来信: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工厂的女工、在婚礼上突然逃跑的新娘、将“拥有500万资产,性能力正常”作为条件在网上征婚的中年女人、东北偏远山村里唯一的女教师、沉迷“哈韩”追星的女大学生、将高薪工作辞掉跑去国外学习西点的公司高管、中国首批开始学习测谎仪知识的女警官……
通过那些来信,张越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平凡人的故事。透过她们,又感知了历史的进程、岁月的变迁,以及隐匿在时代车辙中的矛盾与纠结。
张越曾参访过一个在县城粮食局上班的女孩,二十几岁,每天唯一的工作内容,就是独自守着一间昏暗的仓库。
在WiFi和智能手机还未出现的日子里,女孩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打发时间的东西,她很压抑,很想逃,但看仓库在当地是一份“铁饭碗”,她也担心外面的世界会让人伤心。
“她每天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张越清楚记得,那间仓库没有窗户,非常安静,只有钟表秒针滴答滴答走动的声音,一股担心忽然涌上心头:“这姑娘的一辈子会不会就这么过去了?”
还有一个在报亭工作的女孩,她告诉张越,自己每天守在不足5平米的报摊上,如果没有人帮忙看店,她连厕所都不敢上。报纸和杂志本是帮助人们开阔眼界的东西,可为什么偏偏束缚了她?
张越到外地采访(图中黄色衣服)
在老一辈人眼中,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都赶上了“好时候”。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物质的不断丰盈会让人满足,同时也容易迷失。
一个女人拥有一份稳定到有些无聊,而且收入并不算高的工作,这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及格的人生”,可她们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真心话总是很难被耐心倾听。
《半边天》节目截图
有一次,张越到山东采访一位爱好打扮,穿着时髦的农村妇女。
白天在地里干完农活,她习惯回家换上旗袍“美一下”,到了晚上再换一身宽松的衣服洗衣、做饭,为此她被村里人唤为“杨三换”。
农妇只有初中文凭,却酷爱写诗,村里人笑话她,家里人也埋怨她瞎折腾。渐渐地,她便不再写了。采访时张越问她,上一次写诗是什么时候?
农妇回答:“在梦里,但是没有爬起来记下,诗就被压死在梦里了。”
《半边天》节目截图
在主持《半边天》的十几年中,许多人给张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便有刘小样。
2001年,张越第一次在观众来信中见到“刘小样”。在那封信中,刘小样写,自己现在正住在一个距离北京1100的北方平原深处,这里的一切都是平的,就连生活也是“平”的。
她说自己很喜欢读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她总是读不到书,所以内心非常苦闷。
最初张越并不觉得刘小样特别,毕竟农村妇女想要学习文化知识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可《半边天》的节目策划察觉到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深挖的选题。
刘小样
这一年冬天,张越与节目组来到了陕西关中平原,见到了“八百里秦川”,也见到了刘小样。
第一次录制并不顺利,面对镜头刘小样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越知道这是对方紧张的表现,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天,她暂停了录制,与刘小样一家人同吃同住,大家的关系变得异常亲密,录制便又一次开始了。
摄像机摆好,张越就位,一切准备就绪,开机,不想刘小样却再次失语了。
在那个下着小雪的下午,张越和刘小样在田边坐了几个小时,可无论她如何引导,对方始终说不出一个完整的长句。
张越采访刘小样
眼见着聊不出什么了,张越想放弃了。她对摄像老师说,去周围拍些空镜备用吧,“太绝望了,觉得这期节目只能这么将就了”。
摄像师离开后,只剩张越与刘小样面面相觑,为了缓解尴尬,张越问:“你总说自己不开心,那怎么才能让你开心呢?打个比方吧,此时此刻你最想变成谁?你就能满足了。”
谁知刘小样想都没想,脱口而出一个字:“你。”
张越很惊讶,问她为什么?刘小样回答:“因为你上过学,你有工作,你有同事,你有朋友,你出过门,你哪儿都去过,外面的事情你都知道。”
可是刘小样哪里都没去过。
在已经过去的三十年人生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田地与灶台,在年幼的女儿眼里,母亲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
刘小样的家距离西安城区不过几十分钟车程,往返车票只需要9元,可在结婚前她竟一次也没有到过西安。
在农村,有钱可以置地盖房,但是不能买书;可以买衣吃饭,但是不能外出旅游。因为只要一个农村女孩流露出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想法,就会被扣上“不安分”的帽子——非议是可以“杀死”一个人的。
刘小样告诉张越,结婚之后,丈夫也带她去过一次西安城里,站在繁华的街道上,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城里的女孩敢穿黑衣服,而且穿得那么好看,那么自信”。
“那你为什么喜欢穿红衣服呢?”张越问。
“可能是想在衣服上寄托些什么吧。”刘小样答:“这里的一切都是土的,如果再穿的和土一样,那就更土了。”
沟通从此顺畅起来,张越明显感觉到,刘小样内心里的一块地方被打开了。在后续的对话中,她感受到了刘小样心中对于大山大海的渴望,也知晓了她不甘只是做一个好媳妇的无奈,她只是不想被溶解在平静且一成不变的岁月里。
“时代都走到哪里了?还要女人总是这样。”这像是在反问张越,又像是一种极为笃定的告诫,人总要向往点什么,刘小样说:
“我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
与刘小样的对话结束了,张越急得浑身是汗。摄像不在,机器没开,如此完美的采访,全都错过了。可就是在此时,她忽然发现摄像师竟躲在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地方,悄悄拍完了全程,“这期节目其实摄像救下来的”。
采访结束后,张越回到了县城宾馆,准备第二天启程回北京。当天夜里,刘小样再次找到了她,哽咽地说:“你忽然地来了,又忽然地走了,就像一场梦,你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
2001年的冬天,张越与刘小样完成了一场极为震撼的对谈,同时也帮助张越捧回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
然而奖杯和荣誉之外,张越更看重的其实是这场对话本身的价值。
《我叫刘小样》播出后,很多观众表示,在刘小样的身上看见了自己、妈妈、姥姥、奶奶的影子。她们出生的年代各不相同,可面对感情、生活的困惑却总有相似。
现实不停赋予个体标签和价值,职场女性、全职妈妈、成功女人、农村媳妇……她们不停地被定义、被解构、被描述,可拿掉这些标签之后呢,她们是谁?
“所以把《半边天》定义为女权节目是错误的。”张越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平权节目。”
它的出现不是为了伸张“你要给我这个权利”,而是要宣扬“我本该拥有这项权利”。
这是一种反省,也是一次自省。
自1994年开播以来,《半边天》的播出时间大多在凌晨或者早间时分,口碑虽好,收视平平。
2010年7月,《半边天》几经改版后,正式宣布停播,这一年,张越45岁。
根据台里的安排,她开始了新的工作,一直到2022年春天,57岁的张越正式从央视退休。
离开电视台之后,她受邀参与了一部舞台剧的演出,和多年前进入《半边天》节目组一样,这次她选择加入的理由仍是觉得“挺好玩的”。
期间,她也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讲起离开《半边天》的日子,偶尔也会觉得遗憾。
第一次读到余秀华的诗时,她的内心就有一股冲动,“如果这是在《半边天》,我一定现在就冲过去找她”;后来她又知道了宋小女,表示“这样的故事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事儿”。
前段时间,张越读完了杨本芬老人的书籍——这位年逾80岁的老人用极为质朴语言,描写了中国农村100年间家族中四代女人的命运沉浮,她倍感震撼。
她想,自己应该去找她聊聊,但转念一想,算了吧,有缘总会再见的。
张越近照
几年前,张越去国外出差时,一位中国留学生忽然扑到她的怀里,激动地告诉她:
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家中重男轻女,所以她一直不受重视。看过《我叫刘小样》之后,女孩便决心要好好读书,就像刘小样说的那样,以后出去看看大山大海,如今她终于做到了。
女学生的出现让张越想起了一个久违的人,那个爱穿红衣,倔强重复“我不接受这个”的刘小样。
那次采访结束后,张越和刘小样始终保持着联系,期间她也曾邀请刘小样到北京参加节目,但大家也只是短暂重逢,而后又归回各自的生活。
《半边天》停播后,张越弄丢了手机,刘小样也再没有主动找过她,二人从此断了联系。
张越、刘小样、白岩松参加活动旧照
2020年,一位记者再次来到陕西,找到了已经“消失”10年的刘小样,并看到了《我叫刘小样》之后的故事:
她的面容没有太大的变化,她的头发仍然黑亮,她的笑依旧灿烂,她的向往仍在外面——
她还是没能走出平原。
好像有点遗憾。
但张越可能不这么想。
因为有些声音能被听见,就很难得。
而有些人,已相忘于滚滚红尘;有些事,已消失于茫茫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