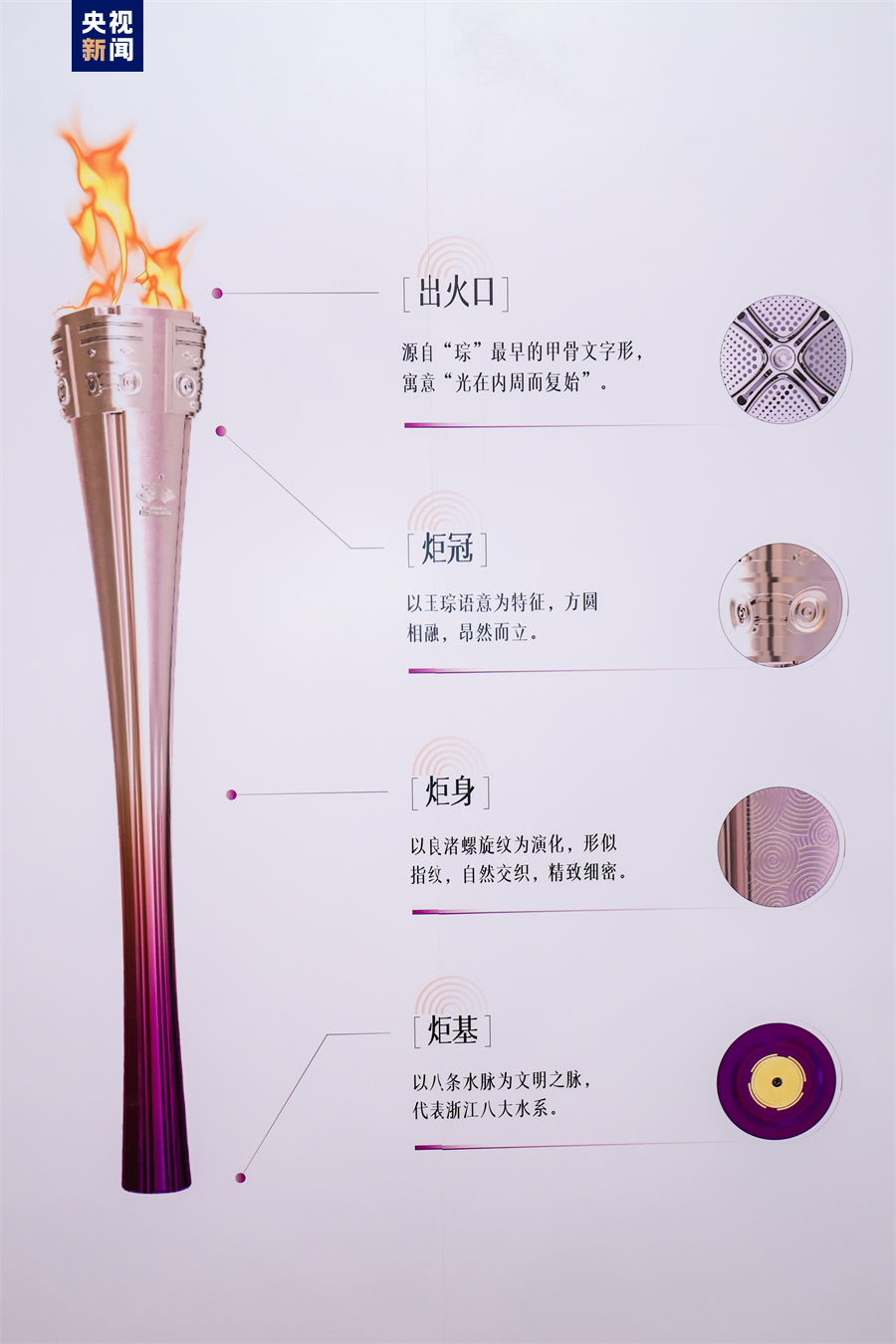布达佩斯40天天气预报、布达佩斯今天天气预报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坐列车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流火季节。
夜车“咔嚓,咔嚓”地大口吞噬着轨道。我躺在包厢的上铺,近在咫尺的是涂满暗红色斑剥油漆的铁天花板,右手边有一盏便利灯,开关已经坏了,床头玻璃搁架的缝隙里,积满了灰尘,床沿只挂下一根边沿被磨出线头的帆布带作保险绳,暗灰色的地毯和浅蓝色的被褥上,散发出微潮且疲倦的气息。看得出来,它已经走了很长的路。这便是东欧国家的列车,带着苏联时代的印记,结实却并不精致。
走廊上的灯已经熄灭,只在近地面处留着一排如节日的彩灯一般大小的地灯,发出莹莹的绿光。大多数人此时已经进入了梦乡,只有几处包厢里还传来轻微的说话声,那是一种圆润的却又略带含糊的音节,想来应该是匈牙利语。
睡到半夜,忽然被一阵使劲地用手指关节敲打着包厢铁门的声音惊醒,随之而来的是有人在门外高声地喊着,“边境检查,请出示护照!”。原来列车此时已经行到了匈牙利边境。
廊道里,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警察正在沿途一个一个地敲开包厢的门。“已经到了匈牙利了。”隔壁的包厢里,有人在惊喜地说。
“卡!”,我的护照在匈牙利签证的那一页被重重地敲上了一个图章。“祝您旅途愉快!”那个年轻的边检小伙子在退出包厢时微笑着对我说,他的蓝眼睛里闪动着善解人意的光。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窗外是广袤无垠杂草丛生的郊区荒地。沿着铁轨线,不时会有一棵棵自由生长的树木擦肩而过。在德国,是看不见这样不修边幅的风景的,几乎每一棵树,每一寸地都被人打理得规规矩矩,整齐有致。东欧和西欧,骨子里还是有差别的。
上完卫生间回到包厢,一位长着花白络腮胡子像极了海明威的老列车服务员推着一辆小车停在门口,“送早餐!”他笑眯眯地递过一个摆得满满的食物的托盘,“想喝点什么?”
红茶,橙汁和咖啡,欧洲所有的地方都一样,永远是这三样作为早餐的饮品。
虽然只有一个烤得松软的羊角面包,可是却附带了那么多的调料:桃子果酱,牛油,奶酪,蜂蜜,巧克力花生酱。欧洲人永远也无法只用糖或者盐做出既本色又鲜美的食物,他们的食品,如果没有了调料,真真味同嚼蜡。酸甜苦辣,都是调味酱汁的功劳。无论什么,用水煮熟了,拿调味酱汁一浇一拌,便大功告成。
吃完早餐,站在包厢洗手台的镜子前擦脸的时候,才注意到原来镜子是一面可以活动的门,镜子后面是一个暗架,架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两瓶小小的矿泉水和两听用纸盒包装的橙汁。应该是随车附送的,可是它们看起来却仿佛是被上一轮旅客遗忘了似的,包装上,落着浅浅的灰尘。
随着“噗”一声泄气似的巨响,列车停了下来,布达佩斯到了!
站台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三五成群地堆挤在一起,不少人就地而坐。随处可见一滩滩水渍的水泥地面上,散落着一些烟头。一些年轻的镶着眉环鼻钉穿着若干耳洞佩戴着巨大耳环露着肚脐化着烟熏装眼圈的女孩子站在咖啡店外,围着半人多高的花岗岩小圆桌抽着烟,旁若无人地飞快地和同伴说着话,上下飞舞的手势好像一只蝴蝶。
忙乱,嘈杂,无序中的有序,这便是布达佩斯给我的第一印象。火车站的地下出站大厅里,排满了充斥着琳琅满目的从亚洲或者土耳其贩运过来的廉价商品的小铺子,有那么一刻,我恍惚是站在国内的小商品市场里,如果模糊了那些金色和亚麻色的头发,忽略了深陷的双眼和高耸的鼻梁。原本一直悬浮在那里的心缓缓松懈下来,那是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忽然逢见故乡的人或物的心情。觉得有趣,觉得讶异,还有一丝丝无法言说的惆怅。
标记着巨大红色“metro”字样的地铁入口处的面包房的柜台前,排着长长的队,一阵阵热腾腾的烘烤的奶油香让再匆忙的脚步也禁不住停驻下来,沾满白芝麻的甜甜圈,铺满cheese和红绿青椒的意大利小pizza,填满熟软樱桃粒的樱桃派,涂满蛋青的表面光滑发亮的羊角包,咬一口会松脆得掉下无数碎屑的千层酥,冰冷坚硬的夹着生菜和salami(意大利腊肠)的三明治,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糕点,挤挤挨挨地站在玻璃柜台里,等待着生人或熟客将它们带走。随着一同上路的自然少不了一杯香浓得刚从咖啡机里调制冲泡出来的浮着一层厚厚牛奶泡沫的macchiato。
适逢上班时间,地铁里站满了人。坐着的站着的,脸上都显出小心翼翼的神情,将自己紧紧地蜷缩在自己的壳里。在欧洲,即使再拥挤的地方,也永远听不到因为被人踩痛了脚而发出的抱怨声。
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个年迈的微驼着背的老妇人,她的脸颊上布满了褐色的老人斑,还有清晰可见的青色的经络,一双像老树皮一样干涸的手紧紧地抓着扶手,她的另一只手里,拎着一个旧布袋子,那是整个欧洲出于环保而设计的购物袋。晃动的车厢让她站不很稳,有人为她让座,可是她摇摇头淡淡地拒绝了。
欧洲的老年人恐怕是世界上最独立最硬气的老年人。除非到了迫不得已,否则,是一根葱都要自己种的固执的脾气。他们谁都不依赖,也谁都依赖不上。孩子们18岁就遵照着社会的规矩离家自立。孩子虽说是自己的,可是,孩子的家,就是另一个天地了,一个他被当作客人来对待的天地。他们却习以为常,因为他们自己和他们上一辈的人,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也得这么过下去。没有人觉得不公平,在小孩子的玩具上都要写清楚所有者姓名的世界里,“自我”就是英文里那个被强调了的大写。
她和我同一站下车,在下车的人潮里,我看见另一个驻着双拐,缓缓前行的老人,她颤颤巍巍的样子,仿佛随时会跌倒,可是,没有人上去表示关切,她努力地一步一步走着,背影里透着坚强。
从网上预定下的旅店是在一条并不算繁华的街上,可是离市中心很近。人行道破旧不堪,如果是在下雨天,那些坑坑洼洼里肯定积满了浑浊的水。街道两边不时可见一些空房子,从破了的窗户里望进去,里面黑森森的,什么也没有。东欧很多人都跑去西欧寻找他们的新生活去了,可是却把房子留了下来。常常听见德国人开玩笑,如果去东欧旅游,其实可以不用住旅馆,随便找一处空房子住就是了。
突然看到一幢房子积满灰尘的玻璃窗上贴着“上海大酒家”的字样。瞬间觉得很亲切。只是如今人去楼空,光景显得很有点凄惨。
欧洲到处是中国餐馆,可是一半的中国餐馆里,都不说中文,微笑着迎出来的只有越南人。正如欧洲的很多寿司店里听不见日文,可是中国人做出的寿司,味道一点也不差。
对照着地图,终于找到了旅店。旅店并没有显目的外观,欧洲很多的小旅店在外表看起来,根本看不出内里的乾坤。样子普通到好像居民住宅。其实也是居民住宅,不过是改头换面过了的。可是欧洲人很喜欢,他们极少去住那些正儿八经的hotel。那样不能算作旅游。他们这样想。
需得整个人压到门上方能推开这扇黑漆大门。穿过一个放着分类垃圾桶的过道,向左一拐,便到了一处楼房的底楼门厅。门厅中央是一架古老的全机械电梯,门和四壁以及地面全是木制的,由人亲自关上才行。狭小的电梯间,仅能容下两人。一盏灯泡在头顶上发出昏黄的光。这样老的电梯,可以想见这幢房子也是年代久远。
虽然整个欧洲经历过二战的侵袭,可是,上了岁数的老房子还是不少,并且依然傲立街头。曾经一个德国人,在吃午饭的时候,很平静地告诉我,他目前住的房子,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了。我诧异得无法言语,然而,他只是轻轻地皱了皱眉头,告诉我除了供暖系统不很灵便,其他的,并没什么特别。
门厅的右边是盘旋而上的阶梯,阶梯的左手边是铸着巴洛克风格的繁缛复杂花纹的冰冷的铁扶手,右手边的墙壁上,铺着苏联时代常见的墨绿色瓷砖。这样的风格,有那么一刻,会让你觉得从楼梯上下来的将会是一位电影中常见的五十年代的穿着布拉吉裙子的烫着大波浪的年轻女郎,她的嘴角,蕴藏着令人愉悦的微笑,可是,眼底却掩饰不住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有的一点忧郁,以及对未来的迷惘。
旅店是改建了一层公寓而来的,在四楼。经营者是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们才出了电梯,他就已经候在门口了。他一边帮我们拿行李,一边用纯熟的英语告诉我们关于住宿的种种事项和要求。
房间虽然只有一个,可是,卫生间,会客区,卧室区,分布得非常合理。最让人欣喜的是,它还在沿墙的一边,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小厨房,微波炉,电灶,咖啡机,洗菜池,操作台,应有尽有,橱柜的抽屉里,锅碗瓢盆干干净净地摆放着。盐和糖也没有遗忘。
这就是欧洲式的旅游,到了一个地方,找一家公寓式的可以做饭的地方安顿下来,然后像当地人一样地生活几天,这样,等到离开的那一天,再也没有一点遗憾。身入腹地的感觉又岂是坐着大巴浮光掠影的人能体会的?
房间临着街,然而没有阳台。欧洲临街的房子大多没有阳台。见惯了国内的住宅,阳台像一个个沉重的口袋挂在房屋一侧,于是就觉得,欧洲的房子,面对着你的似乎永远是背面,但窗沿上摆出来的一捧又一捧的鲜花告诉你,这才是它的脸。
打开窗户,可以听见街道上黄色有轨电车不紧不慢沿着路轨“叮叮”开过的声响,还有汽车轮胎因为速度过快而擦着地面的声音。关上了窗,便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欧洲门窗的密闭性好得惊人。
“如果想洗衣服,请通知我,我会帮你们把洗衣机打扫干净的,还有,这扇门需要用力一点关上。”走之前,年轻的店主认真地嘱咐道,并作了关门的示范。
随着门“砰”地用力关上,两秒钟后,我的心一下子如泥一般松懈坍塌下来,这才感觉到由于走了很长的路,脚底心隐隐作痛。
真的是到了匈牙利了!我一遍遍不能置信地对自己说。电视里,穿着深色西装的播音员正在用匈牙利语播报天气预报。在世界各地的天气栏目里,我找到了慕尼黑,找到了北京,可是没有找到上海。
午后,阳光正艳。我循着地图的路线,去找离住地不远的布达佩斯有名的中央市场。沿着街道一路走去,临街的咖啡吧的户外红绿遮阳伞下,零零散散地坐着人。他们的神情懒洋洋的,那是一种在自己的城市里被宠坏的自得的表情。看着的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生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譬如自己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在这样炎热的让人昏昏欲睡的午后,约了朋友来咖啡店里闲聊,偶尔看见一个带着陌生且拘谨的表情的亚洲女子走过,会怎么样呢?
大部分欧洲人都分辨不出亚洲人的国籍。可是他们会用知道的仅有的亚洲语言对你打招呼。更多的是用一种看着一棵树的目光注视着你,仿佛可以听见他们心里的话:她一定来自很远的地方,可是来这里,做些什么呢?
是啊,坐了9个小时的夜车,跑到匈牙利来,是来做什么呢?答案也许是有的,且近在咫尺。
走了约一站路左右的路程,街道突然开阔起来,原来街道延伸过去,是一座气派高大的铁索桥。四周的人也突然变得多而热闹起来。距离不到桥墩二三十米的街道左侧,看起来像火车站的一幢红砖建筑便是中央市场。透过窗户望进去,里面拥满了人,很像家乡的农贸市场。每一家的货摊上,红红绿绿,不时有拎着沉甸甸的购物袋的人从里面出来,长长的黄瓜和茁壮的大葱从购物袋的边缘伸出脑袋来,浑然不知地向外望着。
可是,我的脚步却在市场门口打了一个小小的弯,我知道自己此刻最想什么。那是我那么多年来一直潜藏在心里的梦想。
去桥上!去桥上!就要看见它了!我忽然有些紧张。一股交响乐的巨大旋律绕着我起舞——约翰•斯特劳斯《蓝色的多瑙河》,这条我曾经在地图上抚摸过无数遍的河流,而今真的近在眼前。
河水并不平静,强劲的风将它的表面吹得仿佛底下暗流汹涌,完全不是我一厢情愿想象的样子:宁静,柔和,温暖,恬淡。它看起来更像一条结结实实的运河,自然,它也不是蓝色的,灰绿色的水,带着一股满不在乎的姿态,往前奔涌而去。
是的,这便是多瑙河了。真正的多瑙河,现实的多瑙河,不带任何童话色彩的扎扎实实的多瑙河。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也许,我从前,是真的误会了很多事呢。
开元周游·开启欧洲旅游新视界
邮箱:huodong@kaiyua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