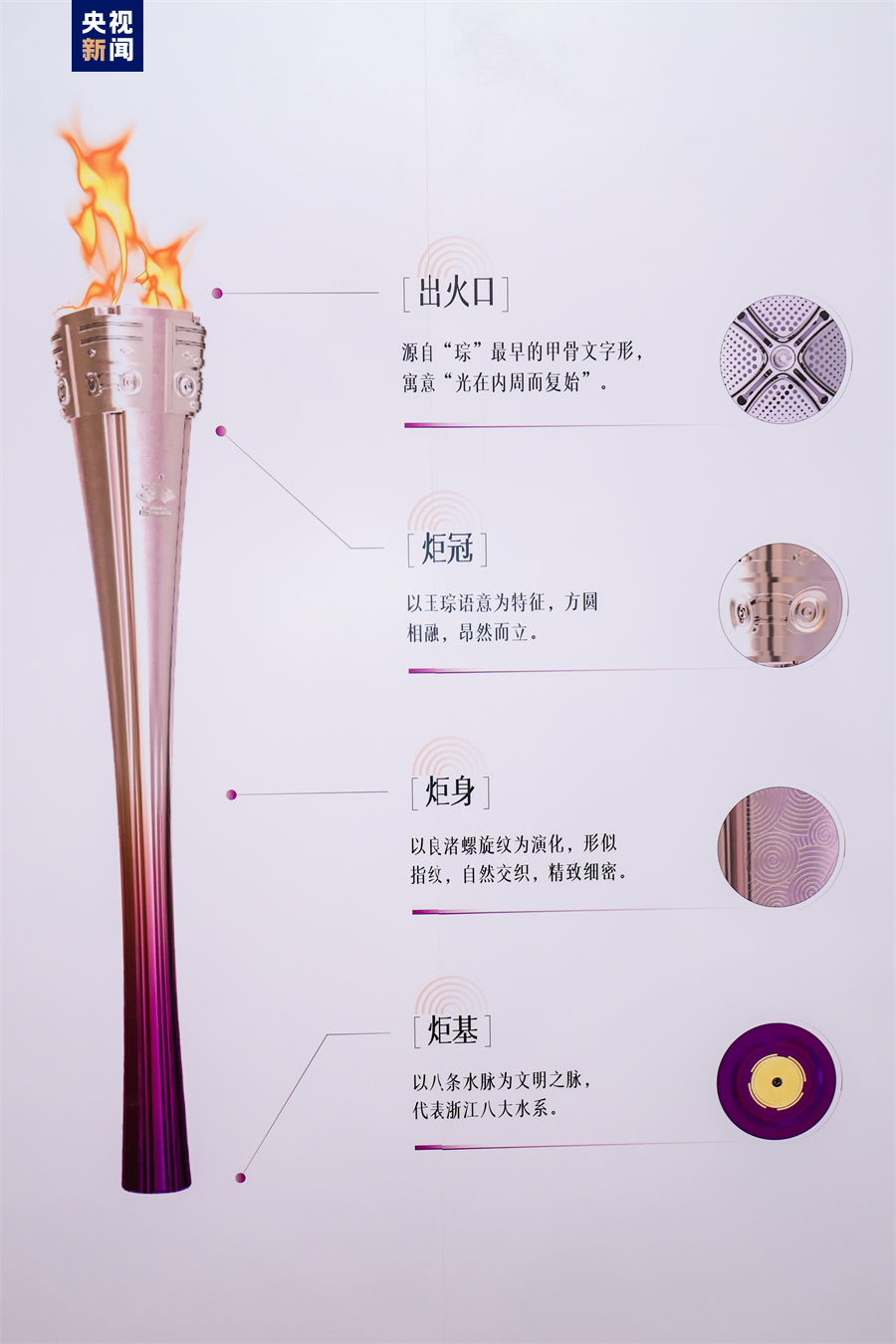其流者怀其源上一句—饮其流者怀其源

为民造福 张 晴书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具有其独特性,千百年以来名士辈出,诗文璀璨,形成了具有世界性、当代性、民族性的当代文化。我的从艺历程,也是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我自幼生活在苏州文衙弄,与明代文征明故居艺圃为邻。自七岁起,祖父便在敦伦堂严格地督导我习书,督促我养成了每天习书的习惯,激发了我学书的兴趣与信心。
每日临帖不是简单地抄书。早晨读帖、白天临帖、晚上默帖,每临一个字皆严格把关,做到一字一关。例如临“天地玄黄”时,若“天”字没写好,那就一遍又一遍地临,直至写好“天”字,方可写“地”字。“第一个字写不好,第二个字很难写好”,这是父亲常叮嘱的一句话。
为了让我在艺术上全面提升,父亲率我拜章太炎弟子毛羽满为师。羽满恩师精诗词、藏书画、善鉴赏,对我做了一个全面的规划与安排:由其教授我声韵,由瓦翁先生教授我书法,由张辛稼先生教授我花鸟画,由吴羖木先生和吴振声先生教授我山水画,由吴吉如先生教授我人物画、古琴和摄影,由张寒月先生教授我篆刻及拓印。
羽满恩师是我父亲的挚友。拜师时,他送我的见面礼便是一本欧阳询九成宫楷字帖,还有一锭从清宫庭中流传出来的烟墨。随后,他带我去拜书法家瓦翁先生为师。羽满恩师当即吟出一联,由瓦翁先生书赠与我。上联为“自是君身有仙骨”(杜甫句),下联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句)。此联寄托了两位恩师对我艺术与人生的厚望。
张寒月先生是印学虞山派的传人,我常去他家学习治印。他为我刻了三方印作为见面礼:“吴门张晴”(赵古泥法)、“张”(圆形姓印)、“日青画”。羽满恩师为我取“日青”之名用于书画。此后,我在书法、绘画及作文时也常用“日青”之名。
为了让我肃敬章氏学业,羽满恩师携我前往章太炎先生老宅,拜见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90多岁的汤先生敏捷且健谈,目光有神,当即送我《章太炎重订三字经》,循循善导,句句诵读。
羽满恩师像个教育总监与督导,全面了解我向各位先生求教的过程。每周,当我完成了各位先生布置的功课,须先面呈羽满恩师,所有作业在获得他认可后,方能去向各位先生求教。当然,各位先生对我的指导内容也会禀告羽满恩师。我自幼习书也极其习惯这种严谨的传统教育模式。
我最喜欢听羽满恩师说民国风云及名人轶事,因为那些人与事都与他有着各种关联。虽然他长年抱病卧床,又有严重白内障,可是他用6B的铅笔写一手传神的张黑女魏碑。笔笔见其铮铮之气,洞其抱朴守拙的气质。
他晚年的诗文和通信由其口述,均由我记录,再用工整的字体誊写清楚,并署名由我誊写。当时孙中山随从秘书田恒先生等常收到由我誊写的书信,他们纷纷来信询问羽满恩师“张晴是何许人,书法写得工整”云云。羽满恩师每每介绍我均是“张晴小友为我声韵之学者,善书画。”由此,我与诸多前辈有了一段“书画忘年交”的佳话。这让我在向各位先生求教与各位前辈交游的过程中,进一步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脉和艺术精髓。
正是因为先生们的悉心教导,让我在诗、书、画诸方面获得了整体进展。上小学时,我的书法与绘画已名列榜首,并在小学五年时进入苏州市环红少年宫美术班和书法班接受正规训练。就读初中时,我对书法和绘画的热爱有增无减,家人反而有了担忧。因我家祖辈一直奉行“工业救国”这一强国理念,希望全家子孙都学工科,而我恰恰把书画艺术当成了主业。这样的压力让我内心激烈动荡,却也坚定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无论家人怎样劝说,我都执意坚持,并立志无论日后发生什么,都要全心全意地走上为艺术奋斗的道路。
父亲虽也劝说,但其内心却喜欢和赞赏我的坚持。事实上,正是他多年的栽培与诸位恩师的培育,为我踏上艺术之路打下坚实的根基。
19岁生日时,羽满恩师赠我一首词,由张辛稼先生书:“年十九,正在用功时,孝以事亲须竭力,郑虔三绝诗书画,学术要精思”,落款为“张晴小友,调寄忆江南,羽满倚声,霜屋老人为之书”。待我长大,分别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求学,分别在方增先老师和卢沉老师门下学习绘画与书法,更加体悟到每个时段恩师教诲的深度与温度。
几十年来,我始终牢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的理念,懂得艺术研究与创作不仅要反映当代生活,还要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今天,我在艺术创作实践与思考中,更加领悟到此话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汲取古今中外文化养分的过程中,我竭力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创新,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力求在笔墨书写之间映带出“中国精神”的源源洪流。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