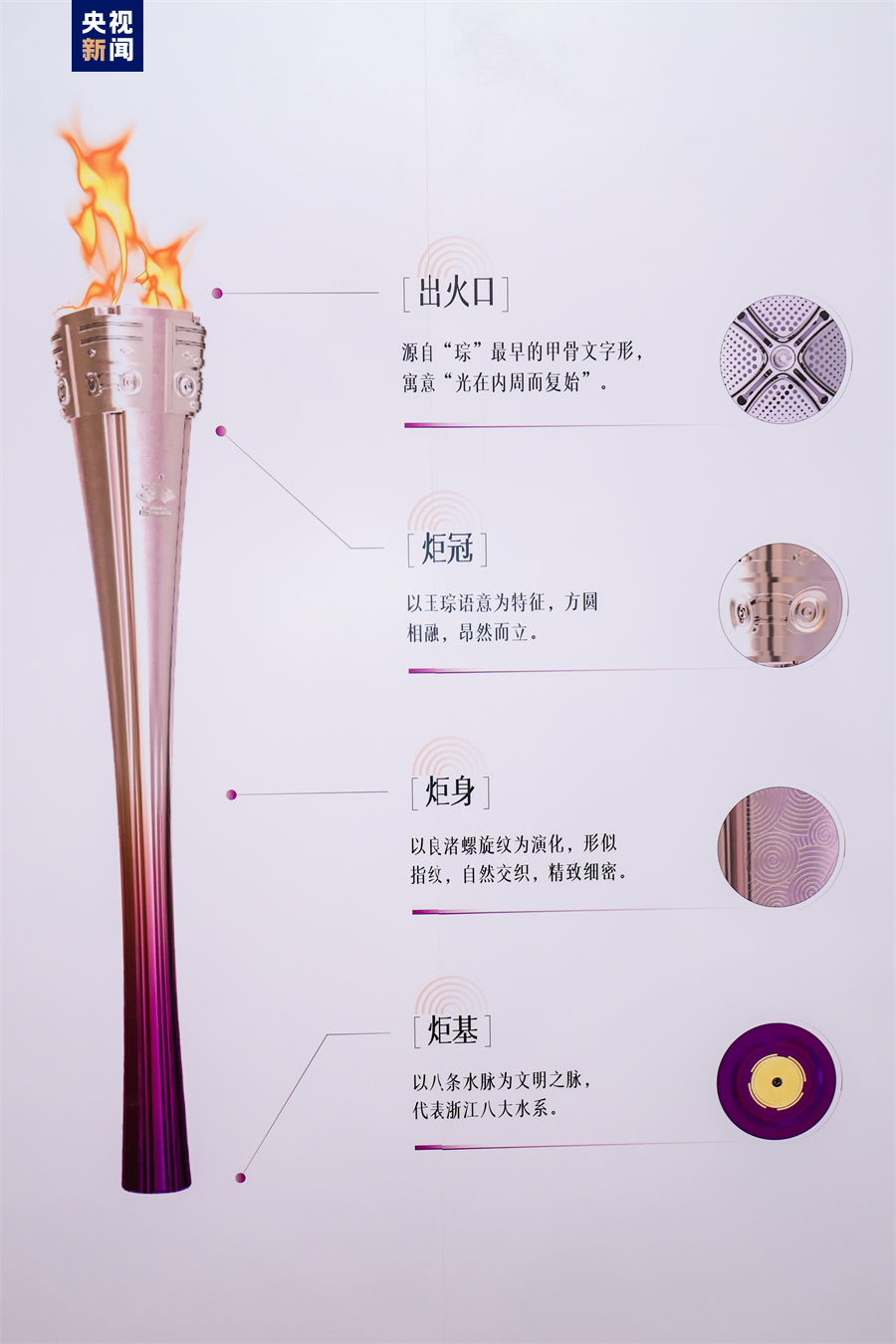你未看此花时王阳明原句-王阳明 你未看此花
《传习录》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的重要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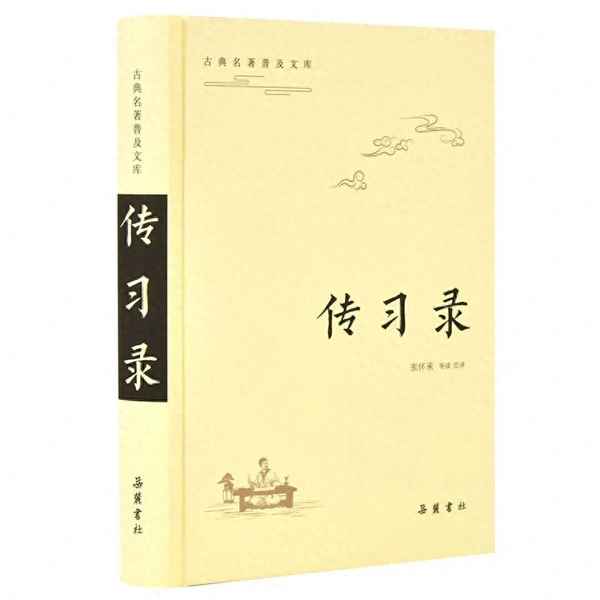
△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 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 年1 月)。弘治十二年(1499 年)进士,历仕工部、刑部,弘治十七年(1504 年)改兵部主事,后因参与反对宦官刘瑾擅权,被系狱,贬贵州龙场驿驿丞。复起庐陵知县、吏部主事、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有功,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因曾筑室会稽阳明洞,创办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遂以阳明行于世。卒谥文成。
王守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明代创建了一个与当时流行的程朱学说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国哲学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奠定基础,经秦汉大一统社会实现思想文化的统一,社会意识形态定儒学为尊。魏晋隋唐的社会动荡,破坏了以维护社会秩序为主旨的儒学的权威,玄学、佛学盛行,这既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多样性,又提升了中国哲学的思辨层次,因而成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重要补充。但是,就对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而言,传统儒学植根于以血缘家庭为基础的小农自然经济,更加贴近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因而有了宋代诸儒对于儒学的复兴。“北宋五子”吸收了佛教、道家的一些思辨方法和理论观点,建立了理学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名教得到了理论的论证与提升,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至此趋于定型。
但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一系,将社会的纲常名教提升到天理本体的高度,对其绝对性、权威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同时也将它们规定为一种外在的绝对,脱离了现实的生命与生活。随着后儒的发展,这种与实际相脱离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少思想家开始对程朱学说进行反思。如明代的陈献章、湛若水等,王守仁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王守仁之所以要建立一个与程朱学说不同的理论体系,除了理论上的探讨之外,还与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感悟密切相关。他在镇压农民的过程中体悟到一个道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深感需要培养人们遵从社会纲常名教的自觉性。在平定宁王之乱后,他便概括出了“致良知”的学说。他力图证明,社会的纲常名教不是某种绝对的外在强制,而是人们心中固有的、内在的道德良知。因此,他要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要求人们去发现、保持并且扩充这一良知,按照这一良知去行动和生活。在此,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王守仁的思想,我们简单地介绍他的几个主要观点。
一、心者天地万物之主
王守仁早年曾经信仰过朱熹的学说,并诚心诚意地按照朱氏的教导去格物穷理,结果却失败了。《传习录》载,他在二十一岁时,认为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为了实践朱熹的学说,便邀一钱姓朋友格其父亲官署门庭前之竹:“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按照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不仅竹子之理没有格出来,而且两人都积劳成疾,这就使王守仁感觉到朱熹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于是便开始了新的理论探索。当他由京城贬到贵州龙场之后,终于领悟到“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卷,以下引王守仁语,凡出于《传习录》者不再注出),完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转折。
在本体论上,王守仁遵循的是思孟、陆九渊的理路,提出“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命题。他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答聂文蔚》)这个“我”当然不是简单地指现实存在的肉身的我,而是指一种主观精神,即心。故他又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微处,是人心一点灵明。”这种思想是对陆九渊思想的发展。
王守仁讲的“心”是指什么?简单地说,是一种精神实体。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直是用来表述思维的器官,如孟子说“心之官则思”,荀子将思维器官分为“天君”(心)和“天官”(感官)。王守仁则认为,心不仅仅是思维的器官,从本质上说,心是一种精神。他明确指出:“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心不是生理器官心脏,而是知觉,是精神。他把这一主观精神视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主宰。他说:“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视听、言动、痛痒等感觉不是心来完成的,但这些现象和活动的“所以”者,即决定、主宰者却是心。心不依赖于感觉而主宰感觉。
在王守仁的思想中,心不仅是身之主宰,而且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传习录》载:“‘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这段话将王守仁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心是一个灵明,不是思维的脏器,心是人的主宰,人又是天地之心,所以,人心就是天地之心。在此,天地之心是指宇宙的核心和主宰。天地万物都以心为存在的根据,离开了我的心,天地万物不仅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以,王守仁又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从王守仁心学的社会意义而言,他的主观目的是要破心中贼,为了破就得立。他所立的就是人们的道德良心,所以,心就是中世纪道德精神在人的本质中的凝结,是人的本质中固有的规定。于是,王守仁又将心称之为“良知”。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孝弟、恻隐之仁等皆为我心所固有,换句话说,这些社会道德纲常原则就是人的良知,而不是存在于我心之外的某种绝对本体的外在要求,所以,道德只在我心,不假于外。“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不是体现在道德客体身上,而是存在于主体的心中。这就是王守仁心学的社会性质。
二、心外无物
王守仁哲学中的心物关系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在他看来,心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它决定着万物的存在,宇宙间的一切都以人心或者良知为自己的本质和根据。“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离开人的良知,万物就不可能存在。由此,王守仁提出了“心外无物”的观点。
《传习录》有一段很典型的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心外无物的实质,就是把客观事物看作是人的主观感觉。花在山岩中生长,不管你看没看见它、知不知道它,它依然自开自落,不依赖于你的心。所以,王守仁的学生对其心外无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对此,王守仁的回答是:当你没有看见这株花树时,这花对你来说不存在,因为它不在你心中,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否存在。只有当你看见这株花树时,它的颜色、形状才在你心中呈现出来,从而形成关于花的观念,你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花不能离开人的感觉而独立存在(显现),只有感觉它时,它才能够呈现于心中,所以说,事物的存在依赖于人的感觉。我们知道,人的感觉依赖于感觉对象对人的感官的刺激,或者说依赖于人的感官和客观对象的相互作用,如花的颜色、形状刺激人的视神经,从而产生相关的感觉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神经元传递给大脑,经大脑的综合整理,便形成关于花的表象。从感觉的发生可以知道,没有客观的感觉对象,就不可能产生感觉。当然,没有人的感觉器官,也同样不可能产生感觉。这就说明,客观对象和人的感觉器官都是实际存在的。王守仁在这里,是将花的表象,或者说将人对花的感觉、认识当作了花本身。诚然,我们也同意花的表象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没有感觉就不可能产生关于花的表象,但表象绝不是客观对象本身,它只是人的感觉对客观对象的反映。王守仁的思维方式就是将作为实际存在的花转化为人对花的感觉而产生的表象。
由此王守仁进一步指出,所谓“物”,只是人的意识的一种指向。“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大学问》,《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对象世界是绝对理念的外化,是绝对理念自身的对象化,马赫则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王守仁的思想是,心(灵明)作为一种抽象的本体、能动的主体必然会向外发露,而其发露处必有所指,不会像其本体形态那样仍然空悬无著,这个心之所指向者就是物。简单地说,“意之所在便是物”。物是心的显现、呈露,它不在心外,心外无物。
心外无物的理论坚持宇宙万物都存在于人的心中,它的展开必然会产生两个悖论。一是,既然心外无物,那么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心之外别无他物,但是,别人是否有心?万物是否也存在于别人的心中?如果别人的心也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心外无物就不能成立。为了解决这个悖论,王守仁就将这个心普遍化,将“吾心”说成是人人都具有的“良知”。你的心就是我的心、他的心。于是,吾心又成了超越主体的个体性的公共之心。二是,万物存在于我心,如果我死了,万物是否还继续存在?王守仁承认了良知的普遍性,就不得不承认他人的存在;既然他人是存在的,那么,我死之后,天地万物就应该继续存在,至少存在于他人心中。这就使得心外无物的观点同样不周延。王守仁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当他的学生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时,他回答说:“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鬼神、万物尚在何处?”人死了,天地万物的存在当然对他没有意义了,可问题在于,对于死的人没有意义的天地万物并不因为人死了就不存在了。
显而易见,王守仁的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然而唯心主义虽然是一种有缺陷的理论,但绝不是胡言乱语,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对人们产生影响,有其存在的根据。从本体论上说,客观事物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但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对象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那就是我们能够说出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是与人们对它的认识相联系的。我们说它是什么,实际上只是说出了我们对它的认识,而不是说出了事物本身。换句话说,离开了人们的认识(或者说意识),事物是否存在就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出已经被我们认识的一切,我们能够说出的就是我们的认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谓的物,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所以,物是什么的问题,直接受着我们对它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制约。王守仁心外无物的观点,就是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这一事实,其失误不在于他将心与物密切关联,而在于他将这一认识论中的现象推演到本体论之中。
三、心即理
作为明代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王守仁必须回答心与理的关系。他从心外无物的理论出发,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观点。
“心即理”并非陆九渊的发明。早在唐代禅宗大照和尚的《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中就已经提出了:“心即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 陆九渊即受其影响。不过,佛家讲的理是指真如佛性,而陆、王讲的理则是以中世纪纲常名教为现实内容的天理。王守仁说:“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书诸阳伯卷(甲申)》, 《王文成公全书》卷八)理是人心固有的原则,是心的条理性、原则性的表现。
心是什么?心不是一团血肉,是一种精神,是中世纪社会的精神,换句话说,心就是天理。离开了天理无所谓心,离开了心也无所谓天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离心无理,离理亦无心。程朱认为,理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属性。王守仁不同意这种观点。“又问:‘心即理之说,程子云在物为理,如何谓心即理?’先生曰:‘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所谓“心在物为理”,就是说,理是心在物上的表现,事物本无所谓理,人心在物即现其理,物因人心而得其理。
王守仁曾经明确地将“心即理”作为自己学说的基本宗旨。他曾经向弟子们强调说:“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在此,他将自己的思想表述得很清楚,程朱以理为外在的绝对,这就将心与理分作两件事,于是,便导致了人心没有纯乎天理的弊病,从而产生出私心。在这种状况下,道德为外在的要求和强制,循理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对外在价值目标的追求,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就是有限的,属于“袭义”。而心即理的学说,则肯定道德是人内在的本心,德行不是对外在标准的符合,而是内心本质的自然流露,这就更加有利于启迪人们的道德自觉。
四、致良知
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出发,王守仁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既然物与理都不外于吾心而存在,它们都包容在我的心中,因此,认识对象世界及其理,就不是对外寻求,而是向内用功。他说:“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认识论意义是,不仅对象存在的实体、理之条绪是我心的表现和作用,而且关于事物和理的知识也先在地存在于我的心中。王守仁将这种先验的知识称之为“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这种良知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感性或者理性认识,而是一种先验知识。“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亦不杂于见闻”。良知本来自足、完满,不依赖于见闻之知,也不杂于见闻之知。所以,良知不能由对外在对象的认识获得,而只能自己在心上体会。“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它不学而知,不虑而能,是“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大学问》)。
良知是人固有的先验之知,因而,致知就不是对客观对象世界的认识,而是在心上用功。根据这种观点,王守仁反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格物致知的学说。他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大学》讲“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朱熹的解释是“即物而穷理”,即实际地考察客观对象世界,穷究其中所蕴含的天理。而王守仁则颠倒了格物致知的逻辑顺序,他以致吾心之良知为致知,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为格物,将致知作为格物的手段和途径,刚好和《大学》的观点相反。在他看来,格物和致知是一回事,从良知上看是致知(即良心的发用),从物上看是格物(即事物因良知而获其理)。不是主体通过认识客观对象而领悟外在的、绝对的天理,而是客体对象因为良知而获得其理。这是一种主体为客体立法的观点。因此,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格物就是正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大学问》)。经过这种转换,格物致知就从一个认识论命题变成了学命题。“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 格物致知就是用良知去正心,去掉人欲对良知的遮蔽,恢复良知固有的灵明。
王守仁强调“致良知”,凸显了道德生活中的主体精神,张扬的是人的道德自觉。“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它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它一点不得。”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听从良知的命令,按照心中固有的良知去行动,每个人都自为主宰,而不是对某种外在绝对的服从。
五、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左传》和《尚书》就已经对此进行过论述。“非知之艰,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这是从知行的难易分析二者的关系。宋儒则从知行的先后秩序来论述二者的关系。程朱都主张知先行后,认为知为本,行为末;知在先,行在后。譬如行路,须先识得路然后可行。王守仁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别知行为先后,犯了将知行割裂为两件事情的错误。他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可见,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是为了纠正朱学知行脱节、重知轻行、只知不行的弊误。
他认为,知与行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事,而是相互包含。“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首先,知是行的指导意识,行是知的具体实践。人们的行为总是受特定的意识支配的,所谓行为,就是将心中的主意付诸实践。其次,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行为离不开动机,有了一个方案、设计、规划,有了对某种目的的追求,而后才有行为;而行为就是为了实现事先所设计的方案,达到预期的目标,作为行为动机的知实现了,才算是完成。所以说,知包含着行,行包含着知,二者不可截然分开。
在这种相互包含的关系中,知是根本的、主要的方面。王守仁说:“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他的这种论述是缺乏说服力的。人们对好色和恶臭产生的爱慕和厌恶心理,是一种内在的情感,属于知的范畴,而王守仁却将这种内在的情感错误地当作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其实质是将行消融于知之中。
当然,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消行,而是激励人们积极去践行,因此,他强调真正的知识必须付诸实践,不付诸行的知不是真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了就是行了,行了就是知了。
知行问题涉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认识是从客观到主观,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二者有本质的差别。王守仁否定知行之间的根本区别,以知去吞并行、消融行,实际上走上了与其初衷相反的道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就曾经深刻地揭示出王守仁知行合一学说的谬误:“若夫陆子静、杨慈湖、王伯安之为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谓知之可后也,其所谓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犹有其知也,亦倘然若有所见也;行者非行,则确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为行也。”(《尚书引义》卷三)王守仁的知行观是错误的,但是错误的知识也属于一种知识,他所说的行就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实践,而是以知为行。
最后我们还要提及“王门四句教”。王守仁“天泉证道”概括出四句话,被门人视为师门心法:“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是心之本体,它是“未发之中”, 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这种意念就有了善恶的差别,它可以说是“已发”,就有中有不中,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是知之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王守仁的心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以上只是撮要介绍其中几个重要的观点。他的学说,上承孟子、陆九渊,将心性之学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他的思想,也曾给日趋僵化的宋明理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对中国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以自己的良知作为最高的本体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否定一切外在的权威,将天理的绝对性消解于良知的主体性之中,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就王守仁的本意而言,他提出“致良知”的学说是为了将中世纪的道德纲常植根于人心,唤起人们遵循和维护纲常名教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因此,他并没有对良知的内涵作出新的规定,仍然以天理为良知的内容,即以良知为人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然而,当天理由外在的绝对转化为主体的意识之后,不仅使得道德价值原则和标准失去了绝对的意义,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之带上感性的和个性的特征。不管人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心的内涵,离开了现实的感性个人,心便不可能存在。所以,王守仁以天理为人的良知(心),必然蕴含着一般社会道德原则和个体感性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这是隐伏在王守仁思想体系中的自我否定因素,这种内在理论矛盾的逻辑展开,必将导致王学的瓦解。从王门后学中产生的传统思想的叛逆学说,绝不是偶然的。黄宗羲在总结王学发展时指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二)这种思想发展的逻辑,恐怕是王守仁始料未及的。
王守仁的思想不仅对中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周边国家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阳明学传入日本之后,成为与官方的朱学相抗衡的民间学说,后来在明治维新中起了思想指导的作用。到现代,他的心性之学对新儒家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新儒家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都以继承、发扬王学自命,并将心性之学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正宗,而视程朱学说为“别子为宗”。
王守仁一生著述不多,正德十三年(1518 年),薛侃初刻《传习录》三卷,后邹守益等人刻《文录》《文录续编》等。隆庆六年(1572 年),浙江巡抚谢廷杰汇集王守仁的著作刊为《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一至三卷为《传习录》,是王守仁教习弟子时的语录,包括重要的学术书信来往;四至三十一卷,为其书、序、记、说、杂著、奏疏、公移等;三十二至三十八卷为其弟子及时人所撰年谱等资料。因此,《传习录》是代表王守仁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王守仁为了表明他与先贤的思想并不矛盾,还特意编纂了《朱子晚年定论》,收集了朱熹晚年与人论学书信中的部分内容,以证明朱熹到了晚年对自己以天理为本的格物致知之说的改正。《传习录》刊行时,便附有《朱子晚年定论》, 其用意除了调和朱王之异外,恐怕更多地是以朱熹来证明王守仁的正确。
我们选注的《传习录》,即以隆庆本为底本,对勘张立文先生整理、红旗出版社1996 年出版的《王阳明全集》重新予以标点、注释和翻译,以俾这部凝聚民族文化精华的典籍得以流传。我们在整理注译的过程中,也参考了时贤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这本译注2004 年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十多年来,承蒙读者的关爱和出版社的支持,现在修订出版。此次修订对原文再次作了校读,添加了部分注释,也修改了一些译文,并添加了每部分的导读。在修订过程中,虽然只是作了部分改动,但所费的功夫并不比第一次注译时少。尽管如此,这个修订本仍然会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张怀承
2016 年8月10日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传习录》前言
△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传习录》,岳麓书社出版
《传习录》
作 者:[明]王守仁 撰;张怀承 导读 注译
定 价:¥35.00
《传习录》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的重要著作,以“致良知”为中心,建构了一个与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不同的思想体系,其学说上承孟子、陆九渊,将心性之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每一部分设导读,解读此部分包含的哲学思想。采用原文、译文双栏对照排版,译文直译、意译相结合。根据原文合理分段、注释,详略得当。以隆庆六年(1572)刊刻的《王文成公全书》第一至三卷为底本。锁线精装,开本适宜,便于翻阅。封面选用进口特种纸,设计典雅,内文选用特制环保轻型纸,轻便易携。
BBC纪录片《杜甫》刷屏,重读杜甫脍炙人口的伟大诗篇!
教科书里的商鞅变法,你真的读懂了吗?
教育部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
岳麓君倾情推荐这38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