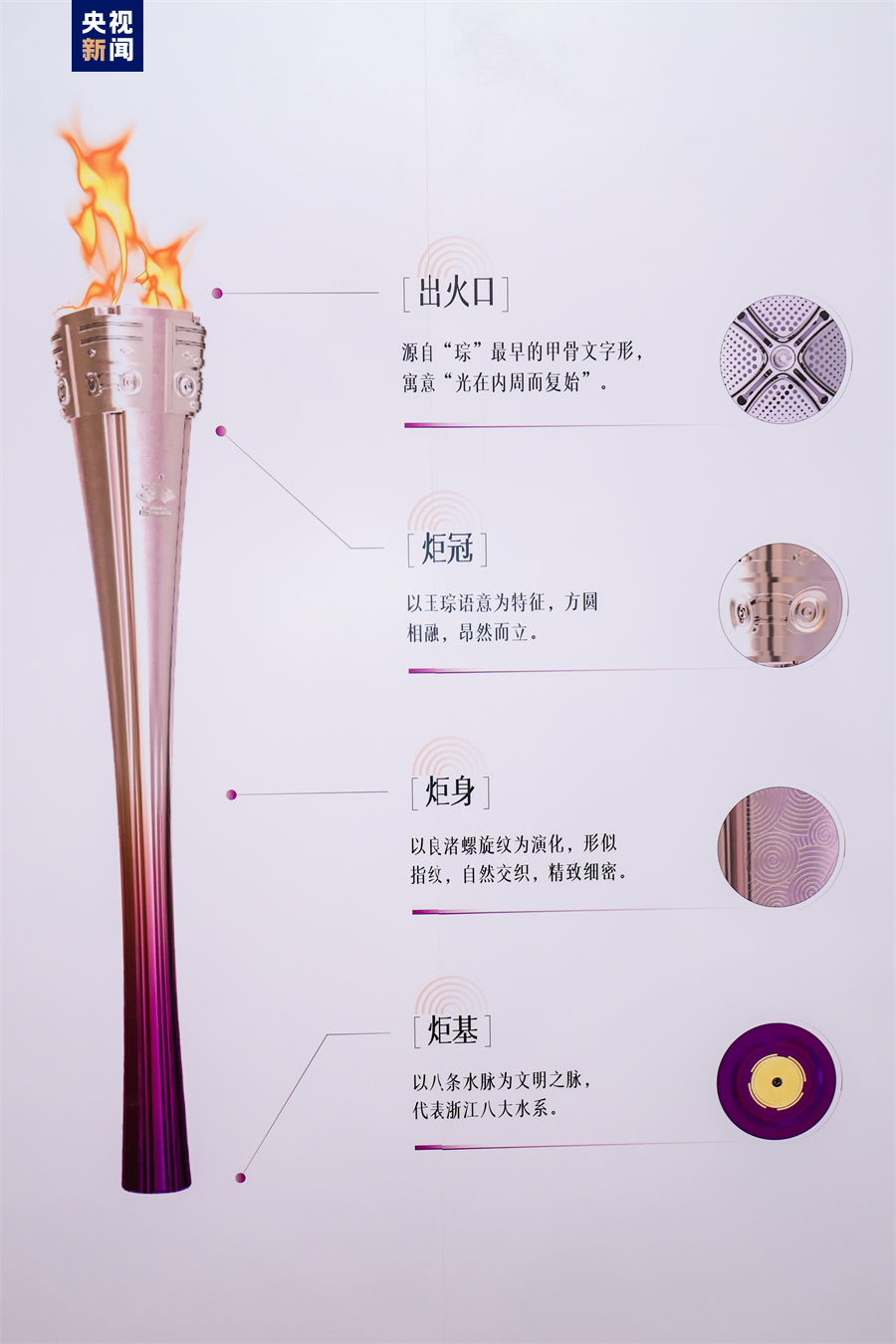辛弃疾的词有哪些特点;辛弃疾最有特色的词
两宋词史上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的词人之一。刘克庄评论辛词:“公所作大声鞺鎝,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夸赞辛词是开山辟路一般的典范。辛弃疾的成就不仅体现在他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
实现了词内容上的变革,为后世开辟新路,将词的创作推向了顶峰。他还将豪放的英雄气写进小家碧玉的词曲之中,刘克庄认为辛词“其纤穠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幼皆成诵”。
辛词中的婉约不弱晏秦,犹如北方八尺铁汉却写得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这样的婉约柔美便已经不同于寻常的婉约艳词了,多出了一层“其潜气内转寓刚于柔的手段与意境”。辛弃疾的一生传奇曲折,加之早年间的军旅生活,更是在他的作品中增添了一种英雄气。

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人生追求鼓舞了后世的爱国志士,且辛词的特色又不仅止步于“豪放”,他能将金戈铁马的英雄气概填入词曲,却毫无浅薄直率之意,读来仍然让人觉得意蕴悠长。
这是辛词用典繁多的缘故,在被后人诟病“掉书袋”的同时,用典繁多也成就了辛词雄奇豪放但仍能保有词曲折柔美之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他数次贬谪还乡、闲居上饶二十年郁郁不得志之时,英雄束手、壮志难酬的无奈充斥内心。
政治生涯的起落浮沉让他极度失望,这时他在词中引入了佛禅的典故,以示看穿世事人生,借此消解心中的痛苦。在现实面前,辛弃疾经历了一个由希望到失望进而陷入绝望的过程,在苦闷、悲愤之余转而面向佛禅之学,希望获得解脱。
使内心中拳拳爱国之心与现实的落差得以平复。但这也只是表面上的心灵安慰,而实质上他仍然无法放下对国事的担忧。学界对于辛弃疾与道家、庄子的关系,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而对于辛弃疾词中体现出的佛禅思想,则并无太多文章对此进行论述。
本文意在对辛弃疾词中的佛禅思想进行初步的整理探究,以求能够更好地理解辛词的思想内涵。
南宋时期,佛道思想大行其道,形成了诸多法门流派,且派别之间也并非相互对立的,常常有援佛入道或者援道入佛的观点出现。士大夫之间也以谈佛论道为雅事,多有儒释道三教兼学的情况出现,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如苏轼就是一个集儒释道三者为一身的集大成者,其晚年诗词创作中也体现出佛家的思想观念。宋代士大夫喜爱以学问入诗,并追求“下笔如有神”的境界,苏轼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
而稼轩则以学问入词,他的禅词大多借景喻禅,即是禅宗所说的“心不孤起,托境方生”。在其词中多次出现《维摩诘经》中的典故,《维摩诘经》以“不二”法门为中心主旨,着意于讨论诸法实相的根本所在,“言语道断,心行灭处,离四句绝百非之不可思议法”。
而将佛法经典作为典故融入词的创作之中,便体现出了佛禅思想对于辛弃疾的影响。辛弃疾在隐居期间,曾有过闭门参禅的实际经历。陆游曾在《送辛幼安殿撰造朝》写到:“十年高卧不出门,参透南宗牧牛话”,说的正是稼轩隐居期间参禅的经历。
也正因如此,稼轩对于佛禅的思想领悟的才更加深刻,也使得禅宗思想自然和谐地融入了辛弃疾的词作之中。如《沁园春·老子平生》一词,“此心无有亲冤,况抱瓮年来自灌园。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慇勤对佛,欲问前因。
却怕青山,也妨贤路,休斗尊前见在身。”这里也体现出了对官场失望后,稼轩归于质朴的田园生活,富贵奢侈必不能长久,而此心已无有分别心,也就没有什么亲疏恩怨的分别了。
可见此时,词中的稼轩只想要放下前尘往事,殷勤佛事,过好自己的田园生活。在稼轩成长的历程中,他学出于儒家,而后出入与佛道,对于佛法的喜爱集中表现于中晚年时期,佛禅思想给了他一个避难的清净之地。
早年间,二十三岁归正,志于北望江山,其精神状态也较为昂扬向上。而在经过七年的宦海沉浮,蹉跎心性之后,也开始生出颓唐之感。
三十岁作《满江红·快上西楼》一词中所写“叹十常八九”这一句,邓广铭先生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中认为是化用的黄庭坚《用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为韵寄李秉彝德叟》诗中句“人生不如意,十事常八九”,这里所写的就是稼轩对于宦海沉浮,世事无常的感慨。
此时的稼轩已经三十岁,《美芹十论》也已呈上,但从此再无音讯,落得个“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的下场。这种对于人生境遇的无奈源于他北伐的愿望难以实现的现实,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他无计可施。
郁郁不得志、壮志难酬的人生经历,也为他后来在思想上寻求佛老,追求内心中的平静自在,埋下了伏笔。
纵观辛弃疾的一生,归隐闲居是无可奈何之举,而佛禅思想已经在闲居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其心态和观念,从而转向接受归隐生活。1182年,稼轩四十三岁,解官归家,居住在上饶带湖,从此开始了在上饶的闲居生活。
《蝶恋花·洗尽机心随法喜》一词就创作于这个时期。法喜以为妻,慈悲心为女”,意为禅宗的方便法门,是万法本根,修行在心,不由在家在庙。一切念头法相,皆由方便生发,见法则喜,见慈悲则爱。
词中所用的“法喜”一词,应是见法则喜之意。这里表现了辛弃疾对于佛老清静无为、念念不住的思想的皈依,想通过修身养性获得健康长寿,表达出一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归于农家田园的归隐心态。
且词中将自己比作陶渊明,“高卧”句化用苏轼和黄庭坚的“溪堂醉卧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风颠”与“微风不动天如醉,润物无声春有功”的诗句,意为不理世事纷繁、宽心自在才是隐逸的长寿之道。
在其闲居期间,上饶带湖地区的自然风光也使其心态从无可奈何、愤懑满怀,转向接受和谐美好的清净农家生活,享受往来种作、鸡犬相闻的乡村美景。
词中也多次出现佛禅典故,用于对清净自然的农家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得心灵平静的描写,因其不着相,不外求,所以花叶不着身,泉鸣不心乱,得见自性般若。但这种清净只是短暂的,英雄年暮,难免还会回忆经年旧事,从而心生悲凉。
辛弃疾与苏轼一样,他一生从未放弃对建功立业,光复河山的渴望,可也如苏轼一样总是壮志难酬。在人生道路郁郁不得志的背景之下,能够与自我和解,自然得益于他归隐田园的人生态度,而这样的态度也正是源自他对佛禅思想的潜在承继。
在这种闲居的乡村生活中,辛弃疾多次访问上饶周边的寺庙,并曾客居于庙中。在此处,辛弃疾置身于自然风景之中,对政治官场感到失望,不想再求取功名,惟愿终老于山寺田园。
词中所提及的“却教山寺厌逢迎”说的就是连山中的寺庙都厌倦了这种往来反复的宦游生活,这也是辛弃疾对于官场心生厌倦的真实写照。山寺田园生活让他忘却了尘世间的种种烦恼,从而获得心灵的疗愈和平静。
且他归正人的身份和北望江山的政治宣言,也使得他在朝中处处受人针对,感叹同道者稀少,只得以松竹为朋、以花鸟为友,逃离官场,寄情山水之间而荣辱皆忘。这里能够看出稼轩心中的态度,他认为无论学道学佛,都是对于人生困难现状的聊以慰藉。
其结果只能是暂时归于平静,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人生的困苦。就如同李太白诗“举杯浇愁愁更愁”,佛道之想都如同杯中酒一般,都只是人生寄托罢了。在辛弃疾看来,佛道的“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并不是真正的出路,都只是暂时躲避之地。
所以,稼轩的心中仍然记挂着天下兴亡,期望光复北地,而他却空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无处施政,这样的困境也就使得他一直在无奈中痛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
辛弃疾对于佛禅思想的表达主要是通过用典的方式,而用典又分为两种方式,即直接用典和间接用典。辛弃疾的用典不同于其他词人,其他词人的用典不及辛词用典密集,且将同一首词中众多用典巧妙搭配,做到雄豪奔放,深厚苍凉。
虽是豪放词却不浅白,典故之间相互呼应,相得益彰;而婉约词中的用典,笔下细腻婉转,俨然一副小女儿姿态,却又能通过用典抒发己志。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词,借女子惜春、想要挽留春天之意,表明自己虚度时光,想要有所作为却不可得。
故有“春且住”之语。又用陈皇后当年旧事,比喻自己空有一身才华和爱国热情,却无人帮助,遭人妒忌排挤。最后用将女子的舞蹈比作政治手段,借杨玉环、赵飞燕的典故,警告奸人莫要得意,自有天理昭昭。
这样的用典和比喻手法,使人不禁想起屈原写《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之时的处境。辛弃疾常常以上述方式用典,典故连着典故,典故套着典故,比喻象征和比喻寄托手法互相联通呼应,使得大量用典显得自然和谐。
辛弃疾也用佛家“不二”之视角看待世界,在《南歌子·玄入参同契》一词中,就用了“参同契”与“不二门”的典故,二者相对呼应。“参同契”是著名道教经典作品,是道教丹鼎派追求炼丹成仙的经典作品之一。
“不二门”指的则是佛教的“不二法门”,语出自《维摩诘经》。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而不二法门乃是得见佛性本性的究竟法门,可直入佛境。其宣扬的是不立文字,无住言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二者互为对仗,在辛词中同时出现,说明辛词对于其认知并非处于宗教信徒的角度,而是取其清净,取其哲理,为的是在诗词中寻找一处可以躲避的清净之地。“细看斜日隙中尘,始觉人间何处不纷纷”。
稼轩的人生过于执着,执着于建功立业、北望江山,而执着则是佛教中所说的人生六苦之一,求而不得谓之苦,是为因果自造,自添烦恼。因这种烦恼无法消解,无处寄存,所以稼轩需要在佛老之间寻求解脱,以期获得心灵的清净与平和。
而间接用典则是将固定的词组典故重新排列或整理,以作者自己的语言方式加入创作之中。如《江神子·簟铺湘竹帐垂纱》一词,其中用到了“病维摩”“散天花”的典故。《维摩诘经》中讲“维摩诘以身疾,广为说法”,这里说的维摩诘生病,不是指疾病,而是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