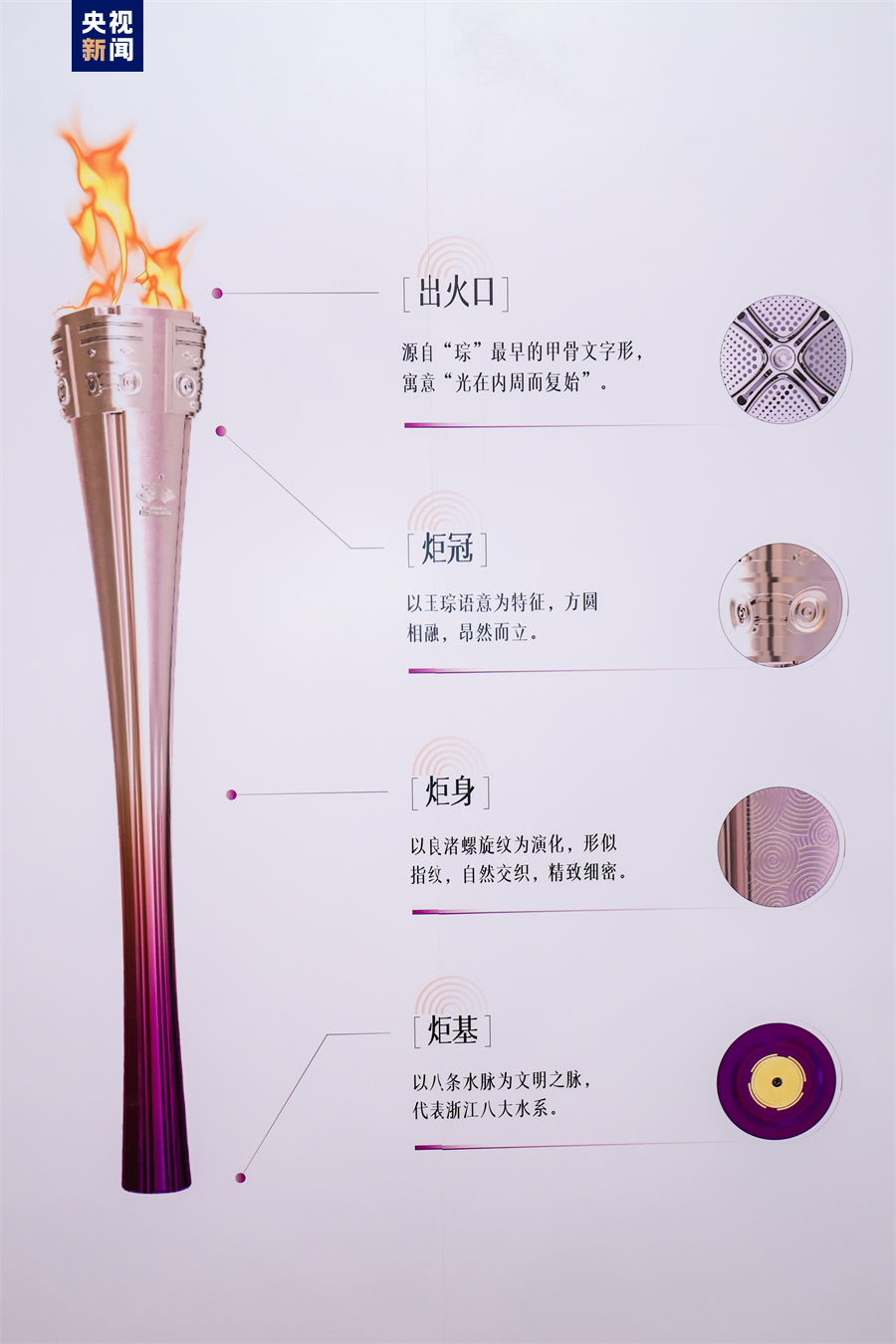雷海宗先生提倡什么观点—雷海为的启示
雷海宗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世人将其名字联成的“声音如雷、学问似海、史学之宗”的美誉,他当之无愧。他的学识、人品和学术贡献的背后,无不体现着他的真性情,然而,这种真性情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暴风骤雨。

1927年,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
1902年,雷海宗出生在河北省永清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雷鸣夏是当地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自幼勤奋好学,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于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22年从清华毕业后,雷海宗获得了公费留美资格,到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
两手空空就能授课
1927年雷海宗留学归国后,先后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
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西南联大,雷海宗的历史教学都非常出色。当时全校性的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分为甲乙两组,为历史系专业学生讲授的列为甲组,由钱穆、吴晗两位老师先后主讲,而为非历史系学生授课的则属于乙组,由雷海宗主讲。
雷海宗是少数能够担任《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两门大课的教授之一,历史类课程的任何一位教授请假,作为系主任的雷海宗都可以临时代课,其效果同样令学生满意甚至惊喜。
雷海宗从来不计较甲组还是乙组,他坚持把自己的课讲好。他声音洪亮,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每节课他都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
听过他课的学生都能描述出他讲课的情形,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十分佩服他这位老师的授课艺术:“一登上讲台,辄口若悬河,从其庞大的知识宝库中掏出的粒粒珠玑连串闪耀,令听众感到内容全面系统,且字斟句酌,无虚言冗语,逻辑性极强。每堂课自成段落,最后画龙点睛,有条不紊,益显其驾驭渊博知识的功力和才识。”
雷海宗的记忆力超强,上课从不带讲义,都是两手空空来到教室,就开讲。学生们认为听雷海宗讲课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而且将课堂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即是一篇首尾兼顾、内容充实且自成体系的文章。
雷海宗讲课有个习惯,每回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经学生提醒后,他便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于漫天战火中,不废弦歌诵读之声。当时,日军飞机常常光顾昆明,投掷。每当空袭来临,昆明人包括联大师生就出城到郊外山谷中躲避,谓之“跑警报”。有一回,雷海宗又如是而问。班里有个女同学,上课笔记甚详,她打开笔记,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一句说‘日机已至,我们跑警报吧!’”艰苦中的乐观和幽默,给了多少学子以信心和力量。
所以,尽管雷海宗在乙组,而选他课的人却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当时已是南开大学的研究生了,但他仍然愿意做雷海宗的旁听生。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大后方的教授们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美国有关方面曾邀请雷海宗等一批名教授赴美讲学,以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改善他们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但雷海宗婉言谢绝了这个机会,决心与全国军民一同抗战到底。
他人口中“最好的老师”
雷海宗教过的学生不仅折服于他讲课的魅力与风格,对他的人品也都称赞有加。因为雷海宗对学生格外关心,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生活。
1932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许亚芬第一次见到雷海宗时,看到他留着平头,身穿一件褪色的旧蓝布长衫,脚着一双尖口布鞋,尽管知道他在国外留过学,许亚芬还是觉得雷海宗不但毫不洋气,反倒更像一位乡村私塾老师。但是,随着上雷海宗的课越来越多,她对他的敬佩和景仰与日俱增。
当时,雷海宗等几位清华教授对指定课外参考书要求非常严格,目也包括在参考书内。而图书馆所备的参考书不论有多少本,总是供不应求。男同学宿舍离图书馆近,他们总是捷足先登,他们人数多,还相互支援。实在没办法了,一天,许亚芬和一位女同学突然想到干脆直接去教授家借书。
雷海宗家住在西院,离女生宿舍很近,许亚芬她们赶到雷海宗家里借参考书,他不但慷慨借书,还请雷师母端出茶点招待她们。后来,许亚芬她们不仅常去借书,有了问题也到雷海宗家去请教。雷海宗总是亲切接待,轻言细语,说古道今,娓娓而谈。每一次同雷海宗交谈,许亚芬都有茅塞顿开之感。有时不知不觉到了饭时,雷师母已悄悄做好了饭。
1934年许亚芬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去青岛市立女子中学任专职历史老师。一年后,许亚芬听说美国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史密斯学院,是专为女子设立的高等学府,该校每年都会奖励五名外国女毕业生研究奖金。许亚芬去信申请,对方回信说除了要求寄去中学、大学的成绩单外,还需要大学主修课程的老师写推荐信。于是,许亚芬立即给雷海宗写信求助,他很快回信答应帮忙,并且直接把自己的推荐信寄到了史密斯学院。几个月后,许亚芬收到了该学院的通知,获得了奖学金,顺利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愿望。
1941年正在西南联大任历史系助教的何炳棣,也是雷海宗的学生。对于雷海宗的品格,他深有体会,他说雷先生最令他敬仰的是他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他一直认为雷海宗是真正兼具和儒家品德的学人,律己极严,终身践行先人后己的原则。但有时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外露。
这年冬天,何炳棣因申请留学失败,很是沮丧。一天,雷海宗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何炳棣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问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为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何炳棣很坚定地回答,他不在乎名义和待遇,在这里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比较好,无意他就。雷海宗这才说出心里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雷海宗的关心让何炳棣心头热乎乎的。后来有一件事,更令何炳棣敬佩不已。三个月后,何炳棣回老家浙江金华,在浙赣铁路上遇见了一位回福建奔丧的学长,他告诉何炳棣,他的路费大部分都是雷海宗老师资助的。
1943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纪念照(前排左二郑天挺,左四雷海宗,左五吴晗)
1946年6月,西南联大复员北上,雷海宗一家由昆明乘飞机到达重庆。当时,重庆到北京的飞机周期很长,而且要按抵达重庆的日期排队。雷海宗一家在重庆等了一个多月,等轮到他们时,直达北京的飞机竟然停航了,他们只得改乘去南京的飞机。到达南京后,京浦路还没有恢复通车,要从上海乘海轮到塘沽,再转乘火车去北京。但去塘沽的船何日起航,却一直杳无音信。他们在南京住了两个多星期后,乘京沪路火车去了上海,再等海轮北上。
在上海又住了两个多星期后,他们才买到去塘沽的轮船票。当时从上海去北方的同学有三四百人之多,都要乘这艘去塘沽的海轮。这些同学本来是由一位教授带队的,这位教授看这么多学生需要照顾,觉着有困难,打退堂鼓了。临开船时,他忽然对雷海宗说:“雷先生,我去不了了,由你带队吧。”雷海宗想到几百名同学不能无人照管,就义无反顾承担起了照顾这几百名学生的重任。
然而,海轮在行驶途中遭遇了大风浪,几乎沉没。面对如此险境,雷海宗毫不畏惧,组织同学分队、分组管理,搞得井井有条,总算渡过了难关。海轮抵达塘沽后,他又组织这些学生坐上火车去北京。火车抵达北京站时已是夜里12点,雷海宗让家人先回去,他留在车站,把每一个学生的行李、去处都安排妥当,他才回家,此时已是凌晨3点多了。
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在北京复校。雷海宗很关心国内外形势和政局的发展,撰写了大量时论性文章。到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有关当局为他提供机票,动员雷海宗“南飞”,被雷海宗拒绝了。他毅然决定留在清华园,迎接解放。
1947年由燕京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的齐世荣,插班入历史系三年级,跟随雷海宗学历史。雷海宗给齐世荣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对学生很亲切,没有架子。齐世荣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一次下课后,雷海宗对齐世荣说,有一个从美国来的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想写关于梁启超的论文,他的中文程度还需要提高,你可以去给他补习中文,借机会练练英文,并增加点收入。齐世荣听后十分感动,也不知道老师是如何了解到他生活困难的。齐世荣有点担心自己讲解不好梁启超的文章,雷海宗鼓励他说:“不要紧,你去试试吧,有困难再找我。”就这样,齐世荣教了这个研究生几个月的中文,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
1952年,随着高校院系调整,雷海宗被从清华大学调到天津南开大学,这多少有发配的感觉,可是雷海宗却乐观以对,他笑着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我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了。”
南开的氛围是相对宽松的,雷海宗在此获得了较多的心灵安慰,他开始在教学及学科建设上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雷海宗到了南开以后,担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持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物质文明史等课程。最初,历史系有位同事教课不受同学们的欢迎,无法教下去。当时雷海宗的课时已排满,但他仍然接下了那位同事的课。这位同事随班听课,雷海宗还得尽量不让他有丝毫难堪。这位同事听课后,对雷海宗大为感佩。后来,在一些场合,他发言时总是说“雷海宗是他最好的老师”。
即便是后来雷海宗患了重病,有人请他帮忙时,他也是不顾病体,热情帮助。一个冬天的晚间,南开大学外语系一位教授因教学需要,来他家中咨询西王母的来历,雷海宗不顾虚弱的病体,滔滔不绝地将西王母的来龙去脉讲到深夜,直到对方完全了解。
因言遇祸
在南开大学,性情简单的雷海宗,只希望能将精力全部用于学术科研活动,其他一无所求。然而现实却给他狠狠上了一课。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雷海宗和全国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心情振奋、知无不言。在天津召开的一次会上,不谙政治风气的雷海宗,还是按照自己的学术研究内容来发表意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但他的讲话不久便被人误解,变成了“承认马克思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很快,报刊即开始了对雷海宗观点的批判。
当年6月,雷海宗在天津史学会讲演“关于世界史的分期问题”时,依然继续按照他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差别不大的观点,这又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经典理论的“修正”。1957年夏,在天津科协举行的反“右派”大会上,雷海宗遭到点名批判并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有几个人也受到牵连。同时,雷海宗受到降职降薪处分,由二级教授降为五级,工资也降了一百多元。
雷海宗先生全家福
这样的处罚对于单纯的雷海宗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雷海宗回到家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妻子说“对不起你”。第二天,他忽然大量便血。此后,雷海宗与夫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过妻子张景茀的陪伴还是给了他很大安慰。有人送来了从香港寄来的饼干,病中的雷海宗一块也不肯吃,全都留给妻子;有电影票、戏票,他总是催妻子去看,并说“你能出去散散心,我就高兴了”;妻子在厨房做饭,他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说:“我不能帮你做,只好陪陪你”;妻子外出回来稍晚,他就在校门内踱来踱去,直到她回来……
此后,雷海宗的教学活动也被勒令停止,但对自己专业挚爱的他,并没有放弃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当时历史系全体教师奉命突击编写一套亚非拉各国历史的书,书稿虽按期完成,但其中错误疏漏特别多,此时的历史系已经无人可以使用,就分配由雷海宗来对该书进行校对。彼时的雷海宗不仅没有资格参编,更不能在书中署名。但他忍着病痛,每天在图书馆里查对英文资料、修补文稿疏漏,为这两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期间,雷海宗还翻译了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的重要章节。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还委托助教从图书馆借出全套《诸子集成》,到了此时,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
重上讲台
1961年末,雷海宗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次年初,戴着“摘帽右派”帽子的他毅然坐着三轮车来到教室,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其中,外国史学史是一门新课,以前各大学历史系都未曾开设过,北大的这门课是由几个教授联合开的,而南开只有雷海宗一人讲授。此时他患上慢性肾炎已三年多了,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四克,全身浮肿,步履艰难。在学生眼里,他虽衰弱不堪,但又极其特别。据当时听讲的肖黎先生回忆: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他讲课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写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腊文。他端坐在椅子上。每当助手写完后,他头也不回,把拐杖往后一甩,有时打在黑板上,然后大声地念着,像朗诵一样,那浑厚的男中音依然那么好听。
每次课后,大概兴奋期已过,雷先生显得非常疲劳。在助手的搀扶下,他拄着拐杖艰难地、默默地走出教室。教室里十分安静、冷漠,既无喝彩声,也无掌声,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然而,学生们也不敢与他接近,一些“左派”在他每次课后还要再安排“消毒”课。在肖黎的笔下,雷海宗的最后一课也显得格外孤独:
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
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这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因尿毒症及心力衰竭,医治无效,在天津与世长辞,年仅六十岁。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8期
作者: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