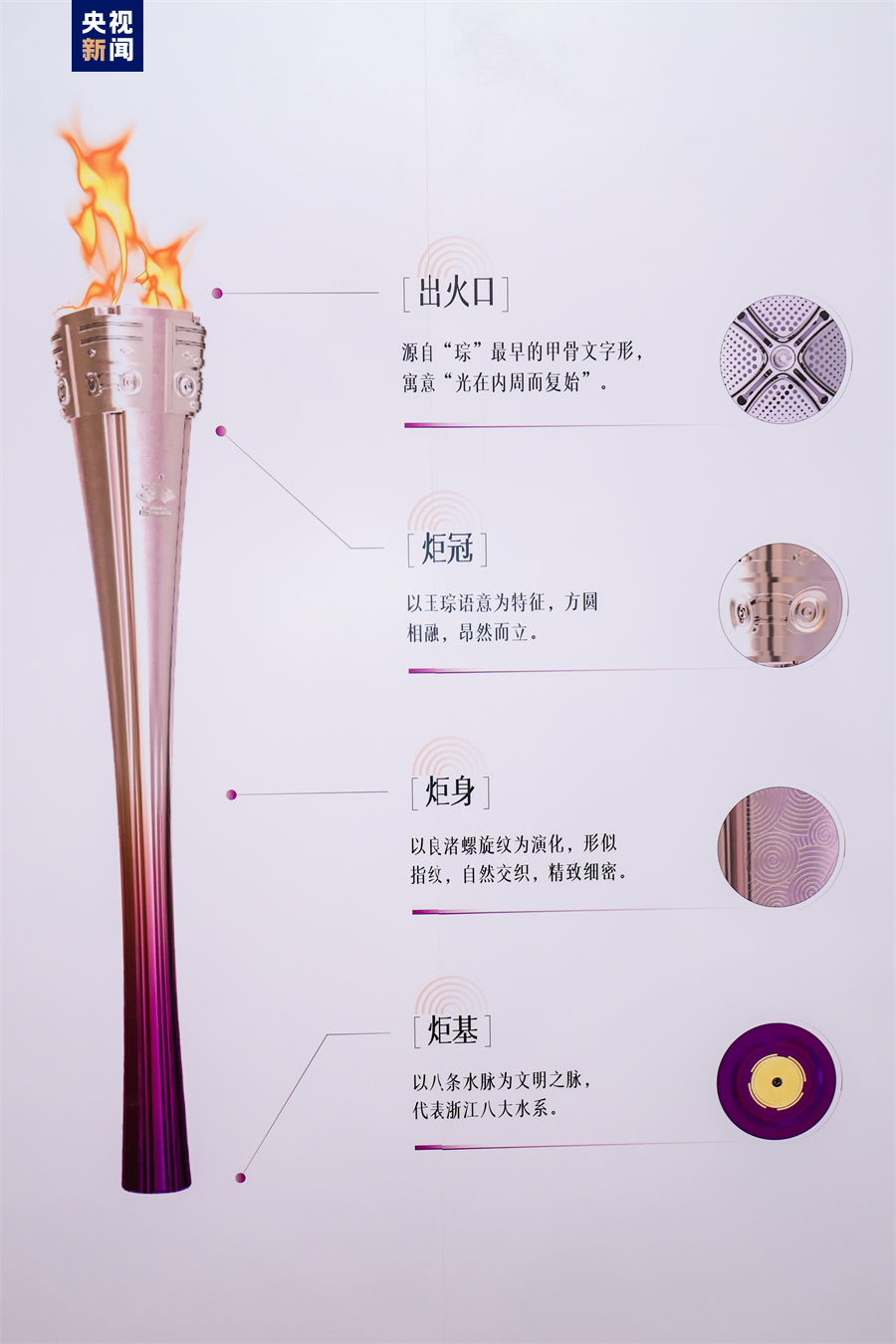海瑞绝后很大原因是他母亲—海瑞最后的下场

这样的眼神是陈洪最不愿意看到的,立刻颤声说道:“这两个太医主子要是不满意,奴才立刻去另找。”
嘉靖不看他了,望着床顶在那里出着神。陈洪屏住呼吸直望着他。
“怎么论的罪,”嘉靖仍望着床顶问道。
“回主子。”陈洪立刻答道,“百官写了奏本,都不愿再说话。更可气的是那个王用汲,连驳海瑞的奏本都没有写,反而呈上了个说宫里矿业司贪墨的奏疏,摆明了是跟主子对着干。奴才已经将那个王用汲也抓了。”
“内阁徐阶他们是什么个意思?”嘉靖的目光倏地望向了陈洪。
陈洪:“内阁的意思,将百官驳斥海瑞奏本里的话都摘集出来交三法司明日定罪。奴才有些担心,那些人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名声,给海瑞定一个不明不白的罪,玷污了主子的圣名。”
陈洪这番话嘉靖其实听不进去,圣名在海瑞上奏疏,后来他亲自公开的时候已经被玷污了。他现在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脸面能挣回来多少,官员里面还有几个能站在自己这边的。
嘉靖两眼又翻了上去,露出了那副怪怪的眼神:“取纸笔来。”
“是。”陈洪立刻站起趋到御案边将纸笔砚盒放进一个托盘中,捧着又踅回到床边,先放到床几上,扶着嘉靖坐好了,然后又捧起托盘呈了过去。
嘉靖靠在床头,拿起了朱笔,想了想,在御笺上先写下了两个字:“好雨”。接着,他的手有些颤抖拉开了这页御笺,又在另一页御笺上写下了两个字:“明月”。搁下了笔:“这里说的是两个人。送给裕王,叫他召徐阶他们一起看。”
“奴才立刻就去。”陈洪捧着托盘立刻应道,接着又轻声问嘉靖,“奴才再请问主子,徐阶他们都指哪些人?”
嘉靖不看他了,望向了床顶:“要是吕芳在,这句话就不会问。”
陈洪不晓事的又一个典型,这话从嘉靖嘴里说出来,就是无比的失望了。裕王平日里和几个师傅们走得很近,这是人尽皆知的,以吕芳秉性是断然不会让嘉靖说明白的。找对人了,是奉旨行事,找错人了,是自作主张,下面的人把锅背了,嘉靖岂不省心?陈洪是揣测不明白,所以才要嘉靖把话说清楚,嘉靖内心的失望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嘉靖突然提起了吕芳,而且那颗头一直仰着望向床顶一动不动,好像吕芳就趴在龙床的床顶上。
陈洪身上立刻像被电麻了一下,回话时居然结巴起来:“奴、奴才愚钝,奴、奴才明白”
到底是愚钝还是明白,这时连陈洪自己也不知道了,将托盘放回御案,捧着那两张御笺梦游般走出了精舍。
裕王府书房
两张御笺摆到了裕王的书案上,由于是密议旨意,陈洪遣走了裕王府当值的太监,自己临时充当起伺候裕王的差使。只见他绞了面巾捧给裕王擦了脸,又拿起了一把扇子站在书案后替坐在那里的裕王轻轻扇着。裕王竟也默坐在那里出神地琢磨着嘉靖写的那四个字,一任陈洪在身边悄然伺候。
自那回裕王性起对陈洪发了一阵雷霆之怒,陈洪跪着向裕王做了一番披肝沥胆的表白,这时裕王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对他礼敬,其实是已经接受了他的投诚。如同山溪之水,虽然易涨易退,一旦流入河中,便再也回不了山中。裕王作如是想,陈洪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徐阶他们来了,竞只有三个人,一是徐阶,二是高拱,第三个却是张居正。
“臣等见过王爷。”三人同时向裕王行礼。
裕王也站了起来,侧了侧身子:“师傅们请坐吧。”
“陈公公。”徐阶三人没想到陈洪也在这里,这时掩饰着内心的厌恶,只好都向他拱了拱手。
陈洪在这里却一脸的谦笑:“王爷说了,师傅们都请坐吧。”
徐阶三人在靠南窗的椅子上坐下了,陈洪却依然站在裕王的身边轻轻地给他扇扇。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望向了裕王。
裕王:“有旨意。”
三个人立刻又站起了,准备跪下去接旨。
“不必跪了。””这回是陈洪开口止住了他们,“没有明旨,是皇上写了几个字给王爷,并叫徐阁老和几位师傅一起参详。一起过来看吧。”
三人这才看见了有两张御笺摆在裕王面前,便都走了过去,
每张御笺上都只写着两个字,字很大,“好雨”、“明月”立刻扑入了众人的眼帘。
裕王见那三人疑惑的眼神便解释道:“皇上说了,这四个字说的是两个人。”
三个师傅都是精读文史典籍之人,看了这四个字,听了裕王一句解释,立刻琢磨了起来,一是在想着答案,二是在想着陈洪在此如何说话?便一时都沉默在那里,裕王看出了三个师傅的心思:“师傅们不必担心。陈公公有陈公公的难处,有些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心里有皇上,自然也有我。当着他有什么尽管说就是。”
三个人有些意外,但看到裕王笃定的眼神,便也信了。
“我有几句话想先请问陈公公。”徐阶望向了陈洪。
陈洪:“阁老请问。”
论年龄,论资历,徐阶都是最长的,他不开口,别人自然也不好说话。
徐阶:“皇上是什么时候写的这四个字,写的时候还说过什么?”
陈洪:“两个太医开了单方,皇上不满意,把他们轰走了。接着问了都察院是怎么论海瑞的罪。”
徐阶、高拱碰了一下眼神,先望了一眼裕王,然后都望向了张居正。
张居正夙有神童之称,聪明颖悟当世无第二人可比,因此徐高二人都想听他的见解。裕王这时也不禁望向了他:“徐师傅、高师傅在内阁主持审海瑞的案子,张师傅是局外人,局外人看得更清楚些。张师傅,依你之见皇上说的是哪两个人?说这两个人是什么意思?”
张居正还是没有立刻接言,谦逊地用目光等着徐阶和高拱说话。
高拱手一挥:“王爷都说了,旁观者清,你就直言吧。”
张居正这才又望向了那四个字开口了:“那我就冒昧了。这四个字说的是李时珍和海瑞。‘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好雨’两字指的当是李时珍。因这两句话里既含着李时珍的时宇,李时珍是湖北蕲春人,又含着蕲春的春字。时当春季便是‘好雨’。龙体违和,皇上想召李时珍来请脉,可又不愿明旨召他,下面两句话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便暗含了这层意思。这是叫王爷立刻急召李时珍进京。”
嘉靖的身体已经扛不住了,宫里的太医不满意,想找李时珍又没法明说,因为他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借机兴风作浪,而且自己修道多年,一直在吃丹药,现在再让太医开药,就是否定了自己多年的修道成果。前面刚被海瑞打脸,后面就自己打自己的脸,这个皇帝还要不要做了。
伴君如伴虎,做皇帝的不容易,做臣子的也难,如果不是满腹经纶,怎么能猜透帝王心思,而且这般刁钻古怪的旨意,哪怕猜错了一次,仕途生涯恐怕就要断送了。
“解得好!”陈洪立刻想起了自己在精舍时皇上曾经提起过李时珍的名字,由衷地赞了一声,转对裕王,“张师傅这一解奴才也想起了。王爷,皇上在精舍时确实提到过李时珍的名字。既然皇上想召李时珍来请脉,又不愿让外边知道,这件事奴才就立刻让镇抚司的人暗中去办,六百里加急,接李时珍进京。”
裕王:“那就烦陈公公去办。张师傅接着说。”
张居正:“既然‘好雨’指的是李时珍,‘明月’说的便是海瑞。‘海上生明月’是祥瑞之象,其间便含着个瑞字。可皇上这时,么会用这两个字来说海瑞,有些费解。”
高拱接言了:“大明之月!皇上这应该是有赞许海瑞的意思,是不是暗示我们在论罪的时候网开一面?”
裕王眼睛慢慢亮了,张居正和陈洪也露出了首肯的神态。只徐阶轻轻摇了摇头。
高拱望着他:“那阁老做何解释?”
徐阶轻叹了一声:“肃卿所解的这层意思自然也包含在这两个字里面。但如果我们按照这层意思去办便会误了大事。”
包括陈洪在内,所有的人都肃穆了。
徐阶:“我的理解,‘明月’两字另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大明无日’!”
众人都是一惊。
徐阶:“明者大明也,后面的月宇却缺了个日字;皇上这是在责备我们这些群臣心目中都没有他这个君父。今日没有叫海瑞到都察院来,皇上已经有了这个意思。”
裕王黯然了,高拱、张居正也黯然了。陈洪望向了裕王。
裕王:“陈公公有话请说就是。”
陈洪:“那奴才就说了。徐阁老,您老的第二层意思是不是想说‘明月’指的是‘秋后处决’?”
徐阶只微微点了点头。
陈洪:“王爷,各位师傅,你们要信得过我,我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裕王:“正要听公公的意思。”
陈洪:“明日三法司定罪的时候,一定要判海瑞秋后处决。”
所有人都不说话,也都不反对,都沉默在那里。
陈洪:“大明朝如今是皇上的天下,将来是王爷的天下,奴才把什么都说了吧。皇上为什么叫奴才拿这个来给王爷看,给各位师傅看,就是要看王爷和各位师傅是不是跟皇上一条心。海瑞如此辱骂君父,百官态度暧昧,尤其那个王用汲,连驳海瑞的奏疏都不愿写,皇上当时听了便有明旨,王用汲要和海瑞一同论罪。这时倘若王爷和各位师傅还不能愤君父之慨,那就真是大明无日了。人人都可以说不杀海瑞,唯独王爷一定要杀海瑞。还有那个王用汲也要重判。”
明明是自己想立威,偏偏说得这般理直气壮。但是歪打正着,陈洪的这番话也救了海瑞一命。
裕王仍然沉默,高拱、张居正也仍然沉默。
徐阶却朗声说道:“陈公公说得极是!王爷,就把我们拟的这两层意思赶紧让陈公公回宫复旨吧。”
裕王仍默默地望着徐阶。
徐阶擅自做主了:“龙体违和,召李时珍刻不容缓,陈公公赶紧回宫复旨吧。”
陈洪还是望着裕王,等他的意思。裕王怔怔地坐在那里:“那就去复旨吧。”
“那奴才便走了。”陈洪说着还不忘跪下来向裕王恭恭敬敬磕了个头,这才站起来疾步走了出去。
陈洪毕竟还是外人,有些话大家不想当着他的面说,先把他打发走了再商量。
“可惜了一个忠臣。又搭上了一个王用汲。”说完这句,裕王便闭上了眼睛。
徐阶和高拱、张居正又对了一下眼神,三人同时显出了一样的默契。
徐阶望着张居正:“太岳,你有何看法,不妨再跟王爷说说。”
张居正:“我理解阁老的意思。这个时候给海瑞定罪,杀是不杀,不杀是杀。”
裕王倏地睁开了眼:“怎么讲?”
张居正:“适才陈公公在这里有些话臣等不好讲。其实皇上这四个字里都含着不杀海瑞的意思,可偏又要看看王爷和我们是什么想法。王爷和我们要是都替海瑞求情,海瑞便必死无疑。王爷和我们若都认为海瑞该死,恩出自上,皇上不准便会不杀海瑞。”
裕王还是心中忐忑:“何以见得?”
张居正:“王爷请想想,海瑞重病是李时珍给他诊好的,海瑞上疏前,家眷是李时珍送走的。皇上这时非但没有任何责怪李时珍的意思,还想请他来诊脉,这便是爱屋及乌之义。‘好雨’二字既说的是李时珍,自然也含有一个海字在内。徐阁老解得好,月字无日,皇上就怕王爷和群臣心中没有君父,现在王爷和群臣都日海瑞该杀,这便是月字有了日字。明日三法司尽管将海瑞定为死刑,将王用汲判流刑。呈奏皇上。皇上不批,海瑞便能不死。海瑞不死,王用汲便也能减罪。”
裕王有些豁然开朗:“徐师傅,是不是这个意思?”
徐阶:“聪明无过太岳。”
高拱接言了:“那我们就干脆在这里给海瑞把罪名定死了,以儿子辱骂父亲的罪名判他绞刑。杀不杀儿子,皆是父亲一句话而已。”
“这个罪名好,就用这个罪名!”裕王拍板了。
这既是文化人,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儿子辱骂父亲确实不应该,但是儿子为什么要骂父亲?做父亲的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吗?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孩子骂父亲是没教养,按照常理来说是父亲没有把孩子教育好,现在因为孩子叛逆做父亲的就把他杀了,这个决心要不要下,就交给做父亲的皇帝来裁决了。表面上看合情合理,实际上暗中抨击了嘉靖没有做好家长应尽的职责。
玉熙宫精舍
三法司会审,照例最后由刑部将结果写成罪案呈奏皇上。
陈洪捧着刑部的罪案从大殿的通道走过来了,进第一道门就看见通道那端一个太监跪在地上熬药,便不进精舍,问道:“谁开的单方,主子验过了吗?”
那人依旧背对着他在那里熬药,陈洪见那人竟敢不回话,背影又好是眼熟,便欲过去。
“进来!”嘉靖的声音在精舍里传来,陈洪不敢再延误,又望了一眼那个熬药太监的背影,只得捧着罪案进了精舍。
嘉靖今天的气色好了些,已下了床,盘坐在蒲团上。陈洪进了门便笑着叫了一声:“主子,刑部将罪案定了。”说着走了过来,双手向嘉靖呈去。
嘉靖不接,只是望着那本奏本。
陈洪翻开了封面:“启奏主子,三法司定的罪名十分明确,那个海瑞以儿子辱骂父亲大不敬的罪名判了绞刑,秋后处决。王用汲目无君父,以朋党罪判杖八十流三千里,也在秋后发配。”
嘉靖望向了陈洪:“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判得十分公正?”
陈洪怔了一下:“主子要是觉得他们判得不对,奴才发回去叫他们重判。”
潜台词,我陈洪觉得罪名合适!如果陈洪觉得判得不对就不会直接来呈报了,这也是在裕王几个人不去当着陈洪的面去商量的原因,这个锅今天得陈洪来背了。
嘉靖:“是叫他们再判重一些还是判轻一些?”
陈洪:“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主子怎么定就叫他们怎么判。”
如果嘉靖一道旨意就行了,还要他们论罪干嘛!
嘉靖望着他又阴阴地笑了:“你何不干脆说好人都让你们去做,恶人让朕来做!”
陈洪扑通一下跪倒了:“奴才,还有群臣都不敢有这个心思。”
嘉靖:“心思都用到天上海上去了,还说没有这个心思。朕问你,什么叫做‘好雨知时节’,什么叫做‘海上生明月’?这些话你昨天为什么不向朕陈奏?”
陈洪的脸色部变了,愣在那里像块石头。
嘉靖:“走了个吕芳,来了个人又想学吕芳。陈洪,你这点德行要学吕芳,连影都没有。吕芳和朕的儿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一点都不瞒朕,你却想瞒着朕。你以为吕芳那样做结果被朕赶走了,那是傻。那不叫傻,那叫‘小杖受,大杖走’。吕芳临走了心里始终明白,不管多少人叫他老祖宗,他永远是个奴才。你以为自己是谁?‘会做媳妇两头瞒’,裕王妃李氏才是我朱家的媳妇呢,她瞒瞒朕倒也罢了。凭你也想做我朱家的媳妇,摸摸你那张剥了壳的鸡蛋脸,够格吗?”
陈洪将捧在手里的罪案放到砖地上,举起手赏了自己一掌,接着又要打。
“不要做戏了!”嘉靖喝住了他,“真要掌嘴就到司礼监提刑司去掌。”
“主子!”陈洪恐慌了,“奴才没有敢欺瞒主子,实在是瞧着主子龙体违和,不忍心让主子再生气。”
“拿朱笔来。”嘉靖不再听他说下去。
陈洪脑子里一片混沌,颤声答道:“是。”不敢爬起来,膝行着到御案前拿起了御笔却不忘在朱盒里蘸了朱墨,双手擎着又膝行着回到嘉靖面前捧了上去。
“罪案!”嘉靖接过了御笔。
陈洪慌忙又捧起地上的罪案用手扶着顶在头上,靠了过去。
嘉靖提起御笔在罪案上划了一把好大的“×”!接着将御笔扔在地上。
皇上勾决人犯照例是在刑部的呈文上划一个勾,要是赦免人犯则将罪案发回重审,像这样划一把叉,却是从来没有过。
陈洪虽没见着嘉靖的朱批,却知道他是在上面划了一把又,怔忡不定,麻着胆子颤声问道:“主子,这到底是勾决了还是没勾决,求主子明示,奴才也好给内阁和刑部传旨。”
陈洪没长记性,想想吕芳在的话会怎么处理!
嘉靖:“他们不是会猜吗?让他们猜去!”
“是。”陈洪这一声答得如同蚊蝇。
嘉靖:“你不是也会猜吗,猜一猜朕会派谁去看大牢,看着那个海瑞和王用汲。”
陈洪立刻在地上磕了个响头:“奴才知道错了,主子的心比天还大,奴才哪里猜得着。恳求主子…”
“猜!”嘉靖喝道。
陈洪定在那里,只好做出副猜的模样,好久才说道:“回奏主子,主子万岁爷是不是叫奴才去看大牢……”
“再猜。”嘉靖的声音益发阴冷了。
海瑞是和嘉靖亲自交手过的,他和王用汲根本不会越狱逃跑,用得着你这个司礼监一号人物亲自看管?
陈洪额上开始滴汗,脑子在这一会儿已经用到了极致,终于想起了嘉靖刚才那句话“吕芳临走了心里还明白,自己永远是奴才”,这才明白,嘉靖一定是对自己打压吕芳的人已经引起了猜疑,咬着牙抬头答道:“回主子,镇抚司诏狱原来一直归朱七管,主子的意思是不是把那个朱七和齐大柱都放了。仍然让朱七去管诏狱,让齐大柱去看管海瑞和王用汲。”
嘉靖的脸色好看些了,声音便也柔和些了:“你不是说朱七、齐大柱都和海瑞有勾联吗?”
陈洪:“奴才该死。奴才当时也是急了,担心宫里宫外勾结了不忠主子。几个月下来奴才都问明白了,除了王用汲,没有人跟海瑞有往来。包括黄锦,不过蠢直了些,当时顶撞了主子,其实也并无吃里扒外的情事。奴才一并恳请主子,把黄锦也放了,让他依旧来伺候主子。”
嘉靖这才笑了:“凭你这点道行都降伏不了,朕早不要做这个天子了。借着海瑞的事在宫里整吕芳的人用自己的人,朕告诉你,吕芳伺候朕四十多年,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人。今天你能猜到这一点,就还有药可救。传旨去。”
陈洪:“是。”满头的汗爬了起来退了出去。
陈洪今天可谓是生死一线。权力是个好东西,当人被权力吞噬的时候只怕连渣都剩不下。
嘉靖望向陈洪刚才跪的地方,见那一块都湿了,可冷汗这时也从自己额间流了下来,一阵眩晕:“黄锦,拿药来…”
黄锦捧着药从精舍门口进来了,一脸的淤青,走路时一条腿还跛着,看见嘉靖满脸冷汗,急忙瘸拐着奔了过去:“主子!”
“慢点走。”嘉靖强撑着兀自关注着他,“当心摔着。”
镇抚司诏狱
一点灯笼光又从通道那头远远地射进了牢房,渐渐明亮。
石姓秉笔太监劝说无效,嘉靖暗访诏狱激怒而去,原来搬进的那张桌子和那把椅子又搬出去了。牢里依然四面石壁,铺着乱草,只是多了一个人,王用汲也上着“虎狼套”和海瑞对面坐在地上的乱草中。
一个小木盆摆在两个人之间的地上,里面还留有一些暗糊糊的粥和一把木勺。
海瑞端着一只缺了口的碗,王用汲也正端着一只缺了口的碗,两人正在面对着喝着碗里的粥。
咔嘣一声,王用汲被一颗粥里的不知是石子还是沙于崩了牙,张着嘴难受地僵在那里。海瑞连忙放下了手中的碗,从地上抓起了一把草窝成一团伸到他嘴边:“慢慢吐出来。”
王用汲吐出了那口带沙石的粥,兀自强笑着:“今日方知民生之艰难。”
早就远远射过来的灯笼光中间停在那里,这时又向牢房这边照过来了,听脚步声好像还不止一两个人。
海瑞:“许多百姓只怕连这个都没得吃。他们要来收拾碗了,赶紧吃了吧。”
“开锁,立刻收拾了。”果然牢门外传来了声音。
王用汲也顾不了粥里的沙石将碗里剩下的粥大口喝了起来,海瑞端着碗却停在那里,慢慢向牢门那熟悉的声音望去。
两只被灯笼映着发光的服这时也正望着他,还闪着泪光,是齐大柱。
二人便这样对视着,海瑞又转回了头,慢慢喝碗里的粥。
“锁钥!”齐大柱喝道,一个锦衣卫牢卒连忙解下了腰间的钥匙,齐大柱一把抓过,去开那把大锁,手竟有些颤抖,钥匙反而插不进锁孔。
“十三爷,还是让小的来吧。”那锦衣卫牢卒又从齐大柱手中接过钥匙,立刻开了锁,牢门推开了,齐大柱大步走了进去。
王用汲已经喝完了碗里的粥,这时也认出了齐大柱。
齐大柱背对着牢门,双手握拳拱在胸前:“奉旨,从今日起由我看管二位大人。”
王用汲目光一亮,转望向海瑞,海瑞这时反而没有任何表情,依然在慢慢啜着碗里的剩粥。
齐大柱转身招呼:“把锁链都开了,洗牢房,将床和桌子凳子搬进来!”
派齐大柱来看管,这就是皇帝的英明之处了,施恩加怀柔,也是给海瑞宽心。
南京卿云号织染坊
“太夫人!太夫人!”高翰文宅里的那个管事在后院进入前院的门口对着海母跪下了,“您老和夫人要这样就走了,小的这只饭碗也就丢了。等一天,最多等两天,小的这就派人请老爷和夫人回来。您老见过老爷夫人再走!”
海母右手拄着枝,左肩上挎着一个包袱,左手还拿着一把雨伞,被那管事跪挡在那里。海妻肚子已经大了,被那个哑女雨青搀着,左肩上也挎着一个包袱,站在婆母身边。
最为难的是李时珍,身上也挎着药囊,一个随从挑着一担木箱,站在他的身后。
作坊前院的踹工染工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全都望着他们几个人。
那个管事跪在那里抬着头:“有哪些伺候不周到,或是有哪个下人给太夫人、夫人脸子看了,告诉小的就是。太夫人大人大量,千万不能这样就走。”说到这里他急着转过头向两个工头模样的人喊道:“还不过来帮忙劝住!”
一个踹工的头儿一个染工的头儿连忙走了过去,也在那管事身边跪下了。
染工那头儿:“太夫人,几个月了,石头也伴热了。蒙太夫人、夫人看得起我们这些下人,大家伙都舍不得你们走,再住些时日等海老爷到南京上任了再走也不迟。”
踹工那头儿回望着满院子的工人大声喊道:“大家都跪了,把太夫人留住!”都是些正在忙活的人,汗渍染迹还满身满脸,这时听到招呼都在院子里跪下了。
海母这时显然也被感动了,望着这些骨子里就亲的人,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慢慢转望向李时珍。李时珍也不知如何说话,低垂了眼。
海母望着大家:“你们的好心老身都知道。可各人都有各人的家,你们都是要养家糊口的人,忙自己的吧。李太医,替我叫开他们,让我们走。”
李时珍只好望向那个管事和那两个工头儿:“太夫人要走谁也挡不住,也与你们无关,你家老爷和夫人那里我会去说清楚。准备车辆送太夫人、夫人去码头吧。”
那个管事望向李时珍:“就不能再留一两天?”
李时珍:“我有急事去北京,太夫人是不愿意再留的。准备车轿吧。”
那管事只好站起了,两个工头也只好跟着站起了。那管事过去接过了海母手中的伞和肩上的包袱,搀着她走下了台阶:“都做自己的事吧。”
满院子的人工都站起了,目送着海母一行穿过中间的石道,向大门走去。
南京运河码头
两条船,一条是李时珍的客船,一条是运货的大船,这时李时珍的那个随从挑着术箱走过跳板上了客船,李时珍却跟在海母、海妻的后面走上了那条运货的大船。
大船的老板立刻迎过来了:“李先生,给太夫人和夫人的客舱都安排好了,您老故心就是。”
李时珍:“先扶着夫人去客舱安歇。”
大船老板:“夫人请随我来。”
老板在前面引着,哑女雨青搀着海妻走进了船舱。
管事搀着海母手里拿着伞和包袱依旧站在大船的甲板上。
李时珍对他说道:“你也回去吧,我有话要跟老夫人说。”
管事将雨伞和包袱放在了甲板上,向海母又深深一揖:“太夫人一路保重了。那个哑女老爷和夫人都说了,就一路伺候太夫人和夫人去海南。一路上的船费和饭食费我们都安排了,到了广州,那边的车船这家老板都会安排好的。”
海母默然了,少顷才说道:“欠你们这么多情,怎么还哪?李太医,告诉汝贤,高家替我们花的钱,一文都要算清楚,还给人家。”
管事还想说什么,李时珍立刻望向他:“你回吧。”
管事又深深一揖,这才转身走向跳板,向岸上走去。
海母立刻握住了李时珍的手:“李太医,我也不再问你了,到了京师,汝贤是祸是福你都要给我捎个信来。”
李时珍黯然了少顷:“现在是什么情形我也不清楚,以刚峰兄的为人,应该不会有什么祸事。倒是嫂夫人的身孕我有些担心。七个月了,只怕到不了海南在路上就会分娩。那个哑女我已经教了她一些接生的事,药我也备下了,万一路上临产,还要靠太夫人把着。”
海母:“上天总有眼的,不会让我海门绝后。”
李时珍:“太夫人这话说得对。可看天命还得尽人事,一路小心为是。晚侄也得拜别您老了。”说着退了一步跪在了甲板上,向海母磕下头去。
海母拄着杖望着他跪下的身影,刚烈的人滴出了老泪。
李时珍站起了:“老板!”
大船老板早就站在船舱门口,这时急忙走了过来,拿起了甲板上的雨伞和包袱。
李时珍:“扶老夫人进舱。我可有话说在前头,一路上照顾不好,我可饶不了你们!”
那老板赔着笑:“李先生言重了,我们会尽心伺候的。”
海瑞已经震惊了朝野,他的家人受到牵连是肯定的。没经历过朝廷风浪的妇道人家,哪里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个时候离开也是不想连累高翰文一家!海瑞的妻子怀着孕,还要舟车劳顿,这里又为后面埋下了伏笔。
镇抚司诏狱大院
画外音:“明制处决人犯分为两种:一为‘决不待时’,朱笔一勾立刻处死,又称‘斩立决’、‘绞立决’;一为‘秋决’,便是在立秋这一天处死人犯,又称‘斩监候’、‘绞监候’。刑部定了海瑞死刑属秋后处决,这一天便是立秋了。”
大院里这棵梧桐树听说是成祖迁都北京将这里定为诏狱时就种下的,二百年了,已是长得杆粗叶大,而且被诏狱的人奉为了神树。这时在梧桐树下已经立好了绞架,粗粗的麻绳绞环已经高挂在绞架的横杆上,绞环下摆着一条踏凳。
立秋的日光特别刺眼,朱七、齐大柱还有几个行刑的锦衣卫这时都站在绞架下,全抬着头望着那棵叶子已经绿中带黄的梧桐树。
两个行刑的锦衣卫抬着一张条案,条案上摆着香炉、香烛和纸钱,抬到了大树的下面。
齐大柱满眼凄惶望向师傅:“师傅,您老问神吧?”
朱七依然抬着头望着树冠:“还不到时辰,再等一刻。”
镇抚司诏狱
牢里摆了两张木床,一把桌子两把凳子,海瑞和王用汲这时对面坐在桌子旁,身上去了锁链,望着桌子上的一碗肉、一碗鱼,还有一碗豆腐,两人却都没有去端酒杯。
“太夫人、嫂夫人应该已经到广州了吧。”王用汲打破了沉默,端起了酒杯,“愿他们一路平安。”
海瑞这才端起了酒杯,两人却谁也不看谁,一口都将杯中的酒喝了。
海瑞拿起酒壶先给王用汲倒满了,又给自己的杯中倒满了,放下酒壶双手端起酒杯望向了王用汲:“圣旨一下,你便要去辽东了。我人送不了你,倘真有魂灵,我会一路先送你去。”说完自己一口喝干了酒。
王用汲却没有去端酒杯,怔怔地坐在那里。
两个人显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玉熙宫精舍
尽管又在吃李时珍开的药,嘉靖的沉疴已经难起,这时已然不能在蒲团上打坐了,靠在床头,大热的天身上还盖着棉被。
秋决人犯的名单摆了满满一御案,黄锦脸上和身上的伤已经好了,只是那条腿从此瘸了,这时跛着站在御案前,从上面挑拣着待决人犯的名单,挨序排来,他的目光定在了写着“海瑞”名字的那份单子上,他的手跳过了那份单子,拿起了排在海瑞后面的几份单子,放在托盘上瘸着腿向床前走去。在床边黄锦先拿起了床几上的朱笔递给嘉靖,然后伸过托盘。
嘉靖平时那两只精光四射的眼像蒙上了一层云翳,这时竭力望着托盘上的名字认清了,才将朱笔勾了下去。几张名单都勾完了,他望向黄锦。黄锦也深望着他。
嘉靖:“还有呢,都拿来。”
黄锦打了个激灵,捧着托盘好艰难地瘸向御案。
镇抚司诏狱院内
“上香,问神吧!”朱七发话了。
两个行刑的锦衣卫立刻点燃了香烛,将线香递给了朱七。
朱七擎着线香在香案前对着大树跪下了:“天佑忠良,该死的不该死的都请上神明示!”祝毕磕了三个头,将线香插人炉中。又拿起了香案上的纸钱,然后站起。齐大柱还有几个人的目光都望向了他。
朱七却望着齐大柱:“海公是你的恩人,这个神你问吧。”说着将纸钱递给齐大柱。
齐大柱接过纸钱去香烛上点着了,手却有些颤抖,放到了地上,然后也跪了下去,
磕了三个响头,猛地站起,走向树干。所有的目光都望向了他。
齐大柱大声喊了一句:“天佑忠良!”接着双掌向粗粗的树干猛地击去。
所有的目光都抬起了,望向从树上飘落的一片片梧桐叶。
无数片落叶都向绞架飘去,一片片都在绞架两边落下了,没有一片飘向绞环。
树上已经只剩下两三片叶子还在空中飘着,齐大柱的眼先就亮了,朱七还有那些人的目光都慢慢亮了。
又有两片树叶远离绞架落在了地上。
这时一阵微风吹来,最后一片树叶眼看已降到了绞环的下边却突然又被吹起了,升上了绞架之上,在那里飘着。那片落叶竟在绞架上慢慢飘着不愿意落了下来!
吹过的那阵风过去了,那片树叶终于慢慢落了下来,却挨着绞绳。所有的目光都惊了。那片落叶慢慢接近了绞环,慢慢从绞环这边飘进了圆圆的绞环绳圈,从绳圈中穿过才慢慢向地面落去。
本来海瑞和王用汲是罪人,作为直接受命于皇帝的镇抚司,敢直接这么祭拜问神,还说出了“天佑忠良”这样的话,也不怕嘉靖怪罪,人心所向已经很明白了。嘉靖贵为九五之尊,身边连个能跟他站在一起的人都没有,一手提拔的陈洪偏偏还不会办事,孤家寡人的苍凉和悲哀也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玉熙宫大殿
黄锦自从赦回,便没有再恢复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的职位,专一在精舍嘉靖身边当差,几十年由两个大太监日夜轮值的制度一改为黄锦日夜十二个时辰陪着嘉靖,晚上也就在嘉靖的床边打地铺。因此,陈洪现在要到精舍见嘉靖一面也都难了,必须事先请奏,准了奏才能进精舍。
这时陈洪就一直待在大殿的门口轻步来回疾走,另外几个当值的太监都低着头站在大殿的门里门外大气也不敢出,等着秋决的勾朱,急送内阁值房。
“到底杀还是不杀?”陈洪站在大殿门外,望着上空的太阳,“什么时辰了?”
大殿内,一个当值太监一直在盯着滴漏的铜壶,这时轻声回道:“都午时初了。”
陈洪转身,走进大殿望向精舍的门。突然,他听见了黄锦的声音,像是在读奏本,仔细一听,是在读海瑞那道奏疏。
黄锦的声调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那种憨直的生气,念得十分慢:“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
“拖时辰吗,”紧接着是嘉靖烦躁的声音,“拿过来,朕自己看。”
陈洪侧着头竖起了耳朵。少顷他又听到了嘉靖的声音:“先把那些该处决的名单叫陈洪送内阁。”
陈洪立刻疾步向精舍的门走了过去,走到门边便看见黄锦踱着脚捧着一个托盘也正向精舍门口走来,托盘上摆着一摞勾了红朱的名单。
黄锦走到了门边,陈洪慢慢伸手去接托盘,凭借黄锦的身子挡着,目光从他的肩上偷偷地向床上的嘉靖望去。
床边高高的立灯十分明亮,嘉靖的脸这时虽被海瑞那道奏疏挡住了一半,但仅从露出的眉梢眼角和紧咬的牙床依然能看出他此时心中透着杀气。
黄锦自经这番磨难,已不再与陈洪说话,这时见他利用接托盘这一瞬间都在偷窥嘉靖,便干脆将托盘往门槛上一搁,跛着脚径自转身向神龛走去,把个陈洪暴露在门口。陈洪这就不能再待了,慌忙捧起了托盘准备悄悄离开精舍的门。
“陈洪。”嘉靖的目光虽然依旧停在海瑞的奏疏上,眼角却扫着了陈洪的身影。
“奴才在。”陈洪连忙跪了下来。
嘉靖还在看着海瑞的奏疏:“徐阶不是说还有要紧的奏本给朕看吗,”
陈洪:“回主子,好像是。”
嘉靖:“好像是就叫他立刻送来。”
陈洪:“奴才明白。”这才站起了,捧着托盘向大殿门口走去。
话里有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干嘛要说“好像是”!陈洪这就很尴尬了。
西苑内阁值房
徐阶淳春芳、高拱、赵贞吉内阁四员会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堂官一早就候在这里,直到这时才看见陈洪捧著托盘出现在门口,便一齐站了起来。
“海瑞勾了吗?”一向沉稳的徐阶这时也沉不住气了,看见陈洪便问。
所有人都望着陈洪。
“都在这上头,我也不知道。”陈洪将托盘往大案上一放。
“一起看,有没有海瑞。”高拱说着便伸手拿过去一叠名单,飞快地一份一份看了起来。
赵贞吉也拿过去一叠,一份一份看着。
果然所有人都牵挂着海瑞,没有先问嘉靖身体状况怎么样!陈洪此时心里有气,拿来的路上他也不先看一眼,刚才在殿外他还心心念念到底有没有勾决,现在却说不知道,明显是跟内阁较劲。
李春芳就挨在徐阶身边,把剩在托盘里的名单拿起一份交给徐阶,等他看完,又拿起一份交给徐阶。
刑部尚书申时行和都察院左督御史大理寺正卿都坐在左侧的案前,这时都望着看名单的内阁四员。
高拱看得最快:“我这里没有。”
赵贞吉那一叠也看完了:“我这里也没有。”
李春芳将托盘里最后一份递给了徐阶,徐阶拿着那份名单停在眼前。
所有的目光都望向了他。
徐阶将那份名单慢慢放回托盘,转对申时行:“申大人,立刻将这些勾决的名单送刑部,午时三刻行刑。”
“没有送镇抚司诏狱的?”陈洪急问。
“没有。”徐阶这才望向众人,“皇上没有勾决海瑞。”
所有的人目光都亮了,互相碰了一下。申时行离开座位走了过来,将又已经摆好在托盘里的名单捧了起来,疾步走了出去。
看着从徐阶到另外几个大臣对名单里没有勾决海瑞都露出欣慰的神态,陈洪心里蓦地涌出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皇上可怜。”他在心里说着,眼里便露出要煞一煞他们兴头的目光,“阁老,勾决不勾决海瑞都在您要呈送的奏本上了。皇上正等着呢,叫你这就送过去。”
陈洪的阴险此时又一次展现了出来。朱批的名单上没有海瑞,此时徐阶要去面圣,陈洪偏偏在这个时候说出“勾决不勾决海瑞都在您要呈送的奏本上了”!万一这个时候嘉靖改变主意了,海瑞被杀了,那就是徐阶的奏本,让嘉靖下了杀死海瑞的决心,这条人命应该背在徐阶身上,不能怪嘉靖。当着内阁的面说出这种话,就是故意要徐阶难堪,救下了海瑞是他徐阶应该做的,毕竟这也是朝中人心所向;海瑞被杀了,徐阶的威望自然也要跟着栽跟头,他以后还怎么统领内阁!陈洪是故意挖坑给徐阶跳!
这几句话说得阴森森的,众人从他的神态中似乎又看到了不祥。
徐阶等的也就是这一刻,警醒到这时离午时三刻还有近一个时辰,皇上会不会在这最后一刻勾决海瑞?全取决于自己如何上这几道奏本,能否奏效,如何说话,皇上此时的情绪至关重要。念想至此向陈洪问道:“圣体眼下如何?”
陈洪:“吃了这几天的药刚见些起色,今日又不好了。眼下正在床上又看海瑞那道奏疏呢。阁老,这个时候犯忌讳的东西最好不要给皇上看。”
“多承关照。”徐阶答了他一句,转对高拱和赵贞吉:“肃卿、孟静,把广东报来那份海瑞妻子死在雷州的奏本和谭纶报来的那份十万匹棉布的奏本给我。”
高拱和赵贞吉都从摆在自己案前的一摞奏本里挑出了一本同时递给了徐阶。
陈洪的眼直勾勾地望着高拱、赵贞吉递给徐阶的那两道奏本。
徐阶接过奏本离了座:“陈公公,走吧。”说着径直走了出去。陈洪只好跟着他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