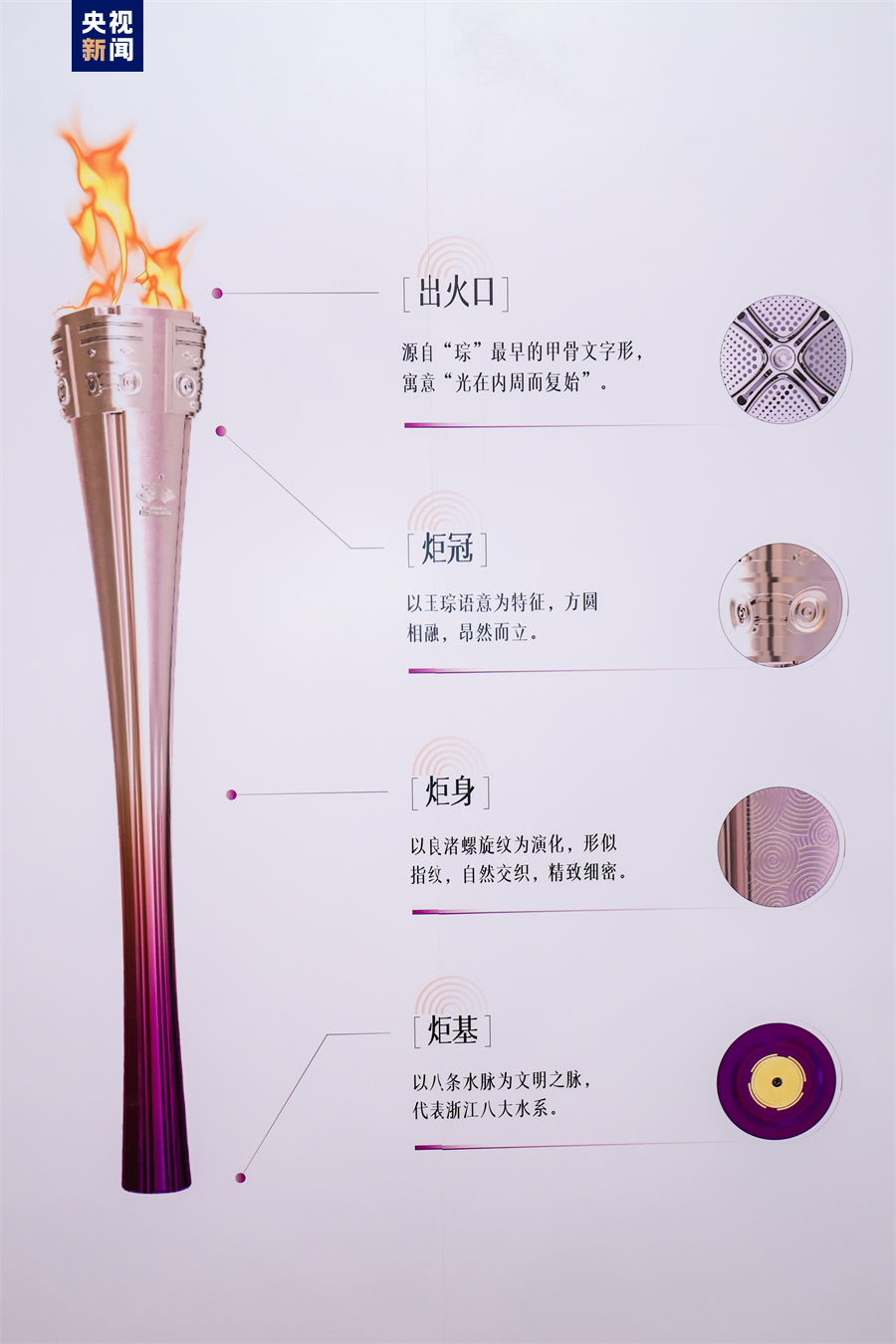鱼游到水面上在干什么;鱼在水面游动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是20世纪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顿河史诗”的作者,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并得到东西方一致认可的重要作家。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耗时14年完成的一部史诗性巨著,作品涵盖了1912年至1922年间俄国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国内战争。
作品以主人公葛利高里的一生经历为线索,揭示了动荡年代下,人道主义思考者的摇摆与迷茫。
葛利高里是生长在顿河边上的哥萨克,他在妻子娜塔莉亚与情人阿克西妮娅之间不断徘徊,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不断挣扎;
葛利高里既是一位英雄,也是一位苦难者,他具有哥萨克人勇敢、正直和不畏强暴的所有优秀品质;
但也具有哥萨克人的所有偏见和局限性,他迷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失在历史快速变化的转折点。
在《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的爱情故事作为对旧的道德规范的挑战,一直是人们所歌颂的对象,这一段悲剧故事也成了反封建思想的壮丽的爱情悲歌。
书中常见的意象也成为学者们把握文本的重要依据,其中“鱼”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不只是作为单纯的景物描写,起到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理的作用;
作为一种“性”的文化符号,“鱼”这一意象的出现更暗合着人物行为的起伏,预示着人物叛逆人格的觉醒与爆发。

对于动物形象的解读在文学文本赏析的过程中一直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文学作品中,动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超越其本身所固有的生物属性,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水平普遍不高的远古时期,“鱼”便成了人们生殖崇拜的对象。
对西方国家来说,“鱼”与原始神话密不可分,因为“鱼的外形与男性生殖器相似,而吞吸水流的行为及腥臭的气味又令其与女性生殖器挂钩,再加之其极强的繁衍能力,‘鱼’便成了丰收神的象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原始的图腾崇拜进入了“由神而瑞”的时期后,“鱼”的形象也逐渐褪去其神性光环,成了“自由与爱情”的象征。
总之,“鱼”作为一种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动物意象,不仅本身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且也暗合着作者与主人公的价值取向。
“渔猎文学”在俄罗斯文学中颇为发达,肖洛霍夫本人酷爱钓鱼,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普里什文等不仅是好的作家,同样也是好的猎人。
可以说,正是“人、野兽、自然”的融合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最主要的特点。
《静静的顿河》虽不能称作传统意义上的“渔猎文学”,但其中大量捕鱼场景的描写,亦与作家肖洛霍夫成长的摇篮——顿河文化的滋养密切相关。
对水的依赖和崇拜感始终流淌在哥萨克人的骨子里,发达的“渔猎文学”的背后,亦隐藏着哥萨克民族热爱自然、追求自由的精神向往。
总之,文学作品中“鱼”这一意象背后,不仅承载着独特的符号功能,更寄托着整个民族特殊的文化情结。
“鱼”这一意象在《静静的顿河》正文中最早出现于第一卷第二章,潘苔莱带儿子葛利高里去钓鱼,并借机敲打他与阿克西妮娅非同寻常的关系。
或许是最终的“战利品”赤红色大鲤鱼使潘苔莱联想到了儿子与邻居的暧昧,又或许潘苔莱本就是带着警告的目的才策划了这一出好戏;
总之,“鱼”在这里的出现,已经具备了朦胧的“性”的意味,为读者暗示出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难以为世俗所接受的两性关系。
真正将“性的隐喻”推向高潮的是第四章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在暴风雨中捕鱼的场面。
“泼剌泼剌”地扭动着光滑身体的鲢鱼、置身于浪涛汹涌中的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潮湿的头发上流溢出的动人气息,构成了一幅充满野性气息的图画。
在这场与自然的搏斗中,胜利属于这一对彼此倾心的年轻男女。
作为“性的隐喻”,捕鱼的情节不只存在于主线故事中。
春心萌动的少女伊丽莎白约米吉卡清晨钓鱼,却在半自愿半强迫的状态下遭到了奸污。
这里描写的鱼不再是灵动活跃的、生机勃勃的,而是成了一种纵欲与犯罪的象征。
如果说,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的爱情是炽热的,充满生命力的,那么作者在描写米吉尔与伊丽莎白这一对时,就显得仅剩野蛮的肉欲。
米吉卡身上哥萨克人骨子里的野蛮与残暴使他在面对伊丽莎白时,就像屠夫宰杀无力的小鱼,这条毫无生气可言的鱼也暗示着伊丽莎白悲惨的命运。
由此可见,作家对于出发点不同的两性关系,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鱼意象”所呈现出的“性的隐喻”,除了作家作为人道主义者,对渴望突破禁区的高尚爱情的歌颂外,也暗含着对卑微肉欲的鄙弃。
在文学创作中,意象的使用应当成为主人公心境、情绪及思想的反映,应当成为寄寓作者理念的“心灵的镜子”。
《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涉及的重要意象有很多,“鱼”便是不得不提的那一个。
阿克西妮娅是《静静的顿河》中的女主人公,是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她与葛利高里的爱情故事被誉为对旧道德准则的挑战,这个悲剧性的故事也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宏大的爱情哀歌。
阿克西妮娅无疑是叛逆的,当她遭到潘苔莱的责难时,她会反击。
阿克西妮娅无疑也是可爱的,为了追求爱情,得到的哪怕只有丈夫的毒打和世人的嘲笑,她也甘愿做扑火的飞蛾。
长久以来忍耐着的阿克西妮娅在见到心上人葛利高里的那天,“一条小鱼在水面上溅起了银色的雨点”,饱受折磨的阿克西妮娅终于感到了一丝慰藉。
她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眼底也总是燃烧恨意的火焰,当葛利高里下定决心抛弃家业和土地,要带阿克西妮娅远走高飞时,她没有显示出一丝犹豫,哪怕面对的是未知的危机与挑战,也甘之如饴。
但是,阿克西妮娅的爱情绝不是的,面对传统宗法观念的挑战,她是人性、光明与自由的象征,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阿克西妮娅成了葛利高里所向往的全部的生活理想。
如果说,阿克西妮娅自出场时便是叛逆者的高歌,那么男主人公葛利高里叛逆人格的觉醒过程便显得阻碍重重。葛利高里的爷爷老麦列霍夫与土耳其女人的结合已然展示出麦列霍夫家族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和对封建道德的反叛,即使这段感情最终还是沦为风俗与偏见的牺牲品。
故事的开始便展现出了骄傲的哥萨克形象,他们敢爱敢恨,是劳动者,同时也是战士。
流淌在葛利高里骨子里的哥萨克的自由、勇敢之血,也使他像不羁的野马般,驰骋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
人向往创造,而时代却总是在压制。
潘苔莱借捕鱼之机对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微妙关系的言语敲打,婚后娜塔莉亚的冷淡与顺从,甚至战争爆发后红白两军的虚伪腐败,无疑都是对葛利高里人格觉醒初期的残忍压抑。
就像总在顿河之水中不断搅动的银白色的鱼儿一样,葛利高里骨子里流淌着勇敢不羁的哥萨克的血液,也在不断推动他做出挣扎与反抗。
这种挣扎与反抗绝不是青春期的懵懂与无知,而是葛利高里作为一位人格觉醒者的叛逆。
不愿服从残酷的生活教条,他与阿克西妮娅一起逃离家乡的土地;不满于非人道的杀戮,他放走了红军的俘虏;
当遭受到白军军官的挑衅与歧视时,他也毅然决然地扬起强硬的拳头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虽然在这一过程中,葛利高里也做出过相当多的让步与妥协,但总的来说,葛利高里的一生,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不断冲破阻碍,追求人格自由的叛逆的一生。
作者通过“鱼”这一意象表现对于人格自由的追求,不仅体现在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人物刻画上,肖洛霍夫对个人生命意志的肯定通过次要人物的故事线也有所表达。
这是达丽亚生命的终结,也是达丽亚的人生态度,宁可失去生命,也要像鱼儿一样追寻自由,保持尊严。
达丽亚与娜塔莉亚的安静沉稳、恪守本分截然不同,她放纵轻浮,逛游戏场,与公婆顶嘴,即使是战争,也无法消磨她自我地活着的愿望,她的死亡是自我选择却也显得那么悲壮。
哥萨克们不愿战斗却始终处于战斗之中,他们对无休止的战争不满,自身却仍然在不断杀戮,锅中的鱼象征着时局动荡下永远找不到出路的士兵;
战争下的哥萨克们难以摆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葛利高里始终在思考的“战争的意义”却始终无法找到答案,但是,哥萨克骨子里流淌的叛逆之血却使他们永不屈服,永远为捍卫哥萨克的荣誉而战。
《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宏伟的著作,以鱼的意象作为切入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背后所蕴藏的精神内核,即动乱年代下,外部世界的压制与思考者寻求出路的尖锐矛盾。
如此,意象便超越了其符号性,更体现出文学意味。
人类的信仰来自对时代真理的渴望,肖洛霍夫在作品中想要传达给读者的,绝不是颓废与靡丧,而是对生活之不朽与胜利的坚信。
当然,《静静的顿河》本身是说不尽的,其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的光辉,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