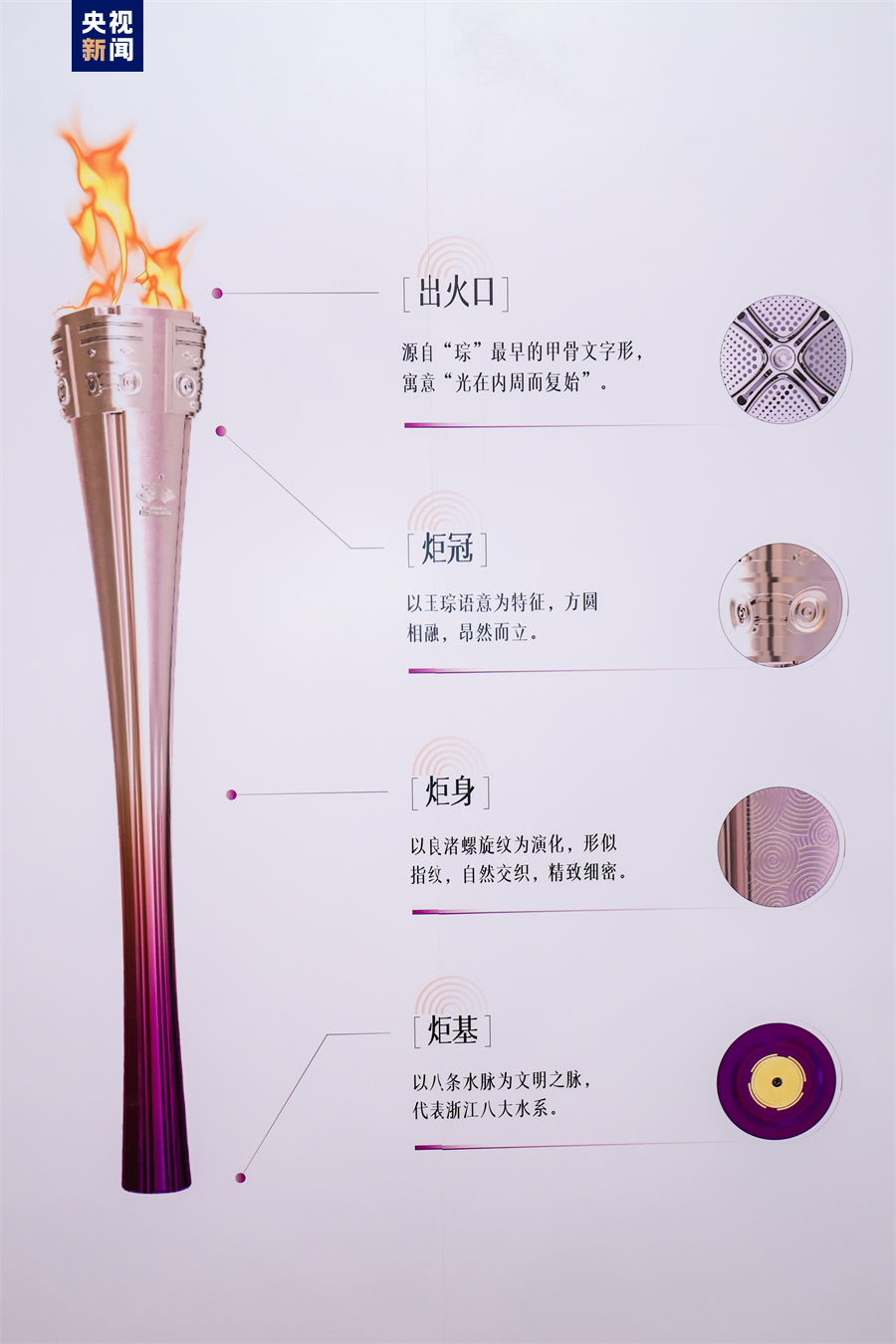身为女性主义者时常感到矛盾,未必是坏事
最近,关注性别议题的人恐怕都对一本书不陌生——《始于极限》。
这本书由作家铃木凉美和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的十二封书信构成,探讨了诸多议题,包括情色资本、女性主义、婚姻、自由、男人等等。每一个书信来回都十分尖锐有力,给人带来久违的充沛的阅读体验。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对国内关注性别议题的人来说,上野千鹤子是一个不用赘述的名字。她在东京大学的演讲曾经刷屏互联网,由她撰写的《厌女》也是许多人的女权意识启蒙之书。相比之下,与她对谈的铃木凉美是个多少有点陌生的名字。
铃木凉美生于东京,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但这样的她却一反常态地选择从事风俗行业,包括在夜总会当女招待,以及AV女演员。
离开“夜世界”后,铃木将自己在AV界的一手观察写成了社会学论文,且凭借研究计划被东京大学录取。今年,她的小说《资优》入围了第167届芥川文学奖。
如此传奇的人生经历,给她带来了许多关注,包括上野千鹤子的。
在出版社的牵线下,二人进行了为时一年的通信。期间,上野千鹤子迫使铃木凉美多次直面自己的痛苦和问题,而铃木凉美也让上野千鹤子不知不觉地敞开了心扉。
铃木凉美
十二轮对话令人意犹未尽,我们仿佛通过一本书,认识了一位远在他国的姐姐。本期《意外的姐姐》,《看理想》有幸联系到铃木凉美,向她抛出了很多我们好奇的问题,或关于书,或关于当下。以下是铃木凉美的回复。
01.
关于个人经历
看理想:其实您的选择可以说是在父权社会下做出的近乎最大程度的叛逆,您有很强的自主性,但是在通信中,上野千鹤子老师又对这些进行了非常犀利的拆穿,指出了更本质的问题。被上野老师揭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感受最为深刻的一次通信或讨论是什么?
铃木凉美:在有幸与上野千鹤子女士进行对话之前,我很抗拒被扣上“弱者”“受害者”的面孔。因为年轻时的我充满了“要充分认识到男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强加给女性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将计就计,反过来利用男人”的气魄,坚信“我是假装被男人剥削,实则剥削男人的强者!”。
这个念头转化成了一种自尊,让我觉得一旦被贴上“被男人剥削的受害者”的标签,自尊心就会土崩瓦解。
与上野女士的通信让我不由得反思,当时我的自尊心看似立得很稳,实则摇摇欲坠,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她指出的恐弱情结上。年轻时的我也在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反抗这个社会的结构,我不能简单地否认这一切,说自己当初的行为是错误的,毕竟那也是一种切实的处世之道。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谢上野女士的指点,要不是她让我直面自己的伤痛,我可能还无法摆脱对男人的过度嘲讽。
这次通信涉及了好几个对我很重要的主题。在关于“母女关系”的章节,上野女士结合自身经历给出了真挚的回复,与读者的反应一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母亲的离去是完全有可能令我失去写作动力的巨大变故,我至今没能理清心绪,而这次通信也为我提供了面对这件事的契机。
看理想: 您的女权意识是如何启蒙的?
铃木凉美:尽管我是个相当靠不住的幽灵社员(译者注:虽然是社团成员,但很少参加过社团活动,像幽灵一样只存在于社团名册上的学生),但我觉得自己姑且算是女权主义者。
在我看来,只要你作为一个女人活在现代社会,完全不参照女权主义就是几乎不可能的。不管你是色情片女演员、陪酒女、家庭主妇还是保守派政客,大家都一样。
对我来说,女权主义者也有“希望让弱者享受到比现状更大的自由”这层含义。我对这一点全无异议,但在“将自己纳入弱者之列”这件事上吃了不少苦头。
看理想:上野千鹤子老师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女性不厌女。如果真的存在不厌女的女性,她们就不需要成为女权主义者。”您在成长过程中,是否觉察过自己的厌女意识?又是如何同这种意识拉锯的?
铃木凉美:回顾当公司职员的那段日子,就能找到不少例子。
当我面对一个立场比自己强势的女性时,哪怕她跟男性一样傲慢,我也会产生比面对男性时更强烈的抵触感,甚至感到惧怕。这也是日本至今难以培养出女性领导的一大理由。女性一旦拥有权力,就比男性更容易被人盯上,在社交网络平台上也会受到猛烈的抨击。这些现象都起因于同一种厌女意识。
与此同时,抱有“女人就喜欢跟女人斗”这种刻板印象的男性也让我烦躁。当时我心想,“我又不是因为她是女人才生气,是对她这个人有意见”,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许只是想安慰自己,“我没有歧视女性的观点”。由此可见,没有女权主义的切入点,这种被不自觉嵌入的意识就很难察觉到。
许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大肆挥霍符号属性的女高中生。那时候,我对那些不愿意被带有性色彩的目光凝视的女性产生了一种别扭的感觉,觉得那是“不自然的”,尽管我当时对此无知无觉。
当年的我好像有一种倾向,对那些明明因为性别占了便宜,却认为自己仅凭能力就能得到认可的女性嗤之以鼻,嘲笑她们“太瞧得起自己了”。这起因于我内心对社会的绝望与成见,也能体现出内在的厌女意识有多么根深蒂固。
长大成人之后,我才逐渐认识到,“有性欲”或“有性属性”与“被人以不礼貌的方式那样凝视”是两回事。如今的我认为,不接受女性内部的矛盾和原本意义上的多样性,在各自的巨大矛盾中努力维持千差万别的自尊和平衡的女性们就很难相互认可。
看理想:从事风俗行业有没有影响您的某些价值观或人生态度?如果有的话,可以讲讲那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吗?
铃木凉美:在夜世界工作的时候,刚离开夜世界的时候,乃至抽身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些经历在上述每一个阶段都对我产生了影响。
在夜世界工作时,我的人生观是“反正这个世界没那么容易改变,人又是愚蠢透顶的生物,我只能想办法在其中找出些许乐趣”。
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摆脱了在光鲜的夜世界获得的这种悲观主义。但是刚抽身的时候,我实在是受够了聚集在夜世界的人的阴暗面,心想“诚实的、纯粹在享受的女生会被吃干抹净,世界是多么残酷啊”。
当了一段时间的报社记者之后,我改行当了作家,如今正以相对冷静的态度重新审视处于伦理边际的夜世界的作用。这是因为审视夜世界,其实也是在审视社会没能准备好的东西,更进一步说,这也是思考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社会的契机。
今天的夜世界有时被称为“必要之罪”(「必要悪」),恐怕是因为它为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找不到容身之地的人提供了暂栖之所,但我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也有贫富差距的再生产和教育问题。
看理想:非常理解您在书中提到的“抵触承认自己是受害者”的心理,同样也被上野千鹤子老师提到的“恐弱”震撼。
您现在会如何处理自己的“受害者”身份?还会很介意这种伤害被男性消费吗?现在对于“恐弱”您是否有了新的理解?您认为“恐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铃木凉美:上野女士点破的“恐弱”二字让我深感痛楚,直到现在都不愿完全承认。“宁愿被当成坏人,也不愿意被看成可怜虫”——不得不说,我这种意识就是所谓的恐弱。
但我总觉得,接纳受害者这一立场,好像就等同于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的选择和意愿的大部分强加给社会,也害怕这意味着将事物简化成非黑即白,对自身的加害性浑然不知。
以不自然的方式冒充强者的我确实滑稽,可话虽如此,要想摆脱已然养成的处世习惯其实很难。重要的是认清自己既有愚蠢的一面,也有被害者的一面,坚持不懈地从这两个角度自省。
思考自己的话,用这种态度就可以了,但是把恐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去思考时,这种感觉就会带来一种副作用,即“通过拒绝受害者的面孔,将本应存在的加害与加害者拖到未来”,这个消极的侧面也需要我们去留意。
事实上,尽管我不认为自己是时代或社会的受害者,但还是一次次被自己的选择和想法所伤害。
因此,在不得不对抗至今没能从心中消失的“我不是受害者”的念头,讲述伤痛时,我会用“这是为了不让妹妹们、女儿们受委屈”去说服自己,这就是我目前用来克服恐弱意识的方法。
02.
关于社会现象
看理想: 近几年,中国年轻女性之间流行起一个词叫“独立女性”,不知道日本年轻人有没有类似的表述?想了解一下当代日本年轻人的性别意识,比起十几二十年前,是在进步、倒退,还是原地踏步呢?
铃木凉美:日本的时尚界终于也流行起了女权主义,尽管比美国晚了20年,抗议、厌恶父权性表达的观点愈发常见了。
最近,就连最保守的时尚杂志之一《CLASSY》的封面上,都会每月出现“时尚与人生都由我做主”这样的文案。这可能与《CLASSY》的同门姐妹杂志《JJ》被迫停刊有关(《JJ》主要面向想要攀高枝的女大学生),编辑部大概是判断出了,渴望当全职太太、渴望高嫁、“把自己嫁出去才是赢家”这样的价值观是不会被当代女大学生和年轻白领丽人所接受的。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能需要更细致的展开,不过我个人认为,时代是在前进的。
在日本,制度层面的进步非常缓慢,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男性育儿假休假率、女性的生育复职率、女性高管的占比等方面出现了细微的变化,而且至少在信息社会中,确实有了更多关于口服流产药、性表达等方面的讨论。
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正处在变化的过程中,社会呈现出了大量带有过渡色彩的侧面。与此同时,我也产生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女性群体在两个极端而直白的符号的号召下一分为二,思维也偏僵化,而这种局面和当年的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把女性的梦想一分为二略有些相似。
过激的观点(既包括激进女权主义,也包括所谓的反女权,即身为女性却同情男性立场或批判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受到青睐,双方本可以分享作为女性的痛楚,却变得咄咄逼人,愈发极端,这恐怕也是社交网络平台的功过。
过渡期的模样总是滑稽的。用慢动作模式播放动画片里的变身桥段,你也许会发现变成超级英雄之前的主人公看起来傻乎乎的。所以意见出现分歧也好,过激派暂时占上风也罢,都不必过于担心。
不过我也觉得,如果一方的“洁癖”太重,另一方则过于“伪恶”,也许女性最后将无法融入任何一方。毕竟人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更渐进包容的态度。
看理想:日本有一档综艺叫《有点心机又如何?》,专门讨论一些吸引异性的“社交小心机”,比如在多人聚会时,可以和有好感的人耳语,以此营造一种私密感;或者穿一些展露身材的衣服。
您如何看待“媚男”和“主动释放性魅力”之间的差异?当一位女性想要吸引男性注意时,难免会以“男性喜欢的方式”呈现自己,这是否代表着她在“取悦男性”,从而没那么“女权”?
铃木凉美:从2005年前后开始,日本女性对“斩男(モテ)”表现出了露骨的关注。在那之前,大家也会用“异性缘好/招桃花(モテる)”来评价他人,会为了提升异性缘悄悄努力,却不会大肆宣扬“这是斩男小心机”。《CanCam》杂志等媒体创造了“超级斩男(めちゃモテ)”这样的流行语,成了这类小心机走到台前的契机。
至于“斩男”和“自由主动释放性魅力”之间有什么差异,这个问题涉及了很多要素,回答起来不那么容易。
首先,露骨的“社交小心机”受到瞩目的时代背景是,女性成为家庭主妇的意愿普遍减弱,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对女大学生而言,“帮忙做家务(译者注:家事手伝い 指不外出工作的待嫁状态)”和“新娘修行(译者注:花嫁修行,婚前学做家务)”已成过去的遗物,所有人都加入了求职大军。那已经不是一个只要被男人相中,就能过上安稳生活的时代了。
换言之,“斩男”的概念是在一个被男人相中也没什么用的时代流行起来的。也就是说,“超级斩男”、“社交小心机”不同于《JJ》高举的、与现实利益挂钩的“合男性口味的女性形象”,并没有实质性的目的。为了让特定的白马王子一见倾心,赢得家庭主妇的地位而装扮自己,注意举止也就罢了,迎合不特定多数人的“斩男心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结合我个人的猜测,“斩男”看似是一种取悦男人的态度,实际却是为满足自己的自尊心和认可欲求服务的流行。
小心机的尽头并没有“被男人选中”这一目的,“就是想得到他人的赞赏”(换成更有时代感的说法就是“想让更多人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给自己点赞”)、“就是想让自己可可爱爱的”这样的念头本身转化成了目的,于是才有了上述现象。
所以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对性主动或性自由的流行。这种行为本身也许算不上“反女权”,因为其目的是取悦自己,而非取悦男性。
不过自我满足的因素仍然是来自他人的欣赏,而且往往是来自男性的欣赏,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些许问题。尽管目的不是依靠男性,但手段也许仍带有依靠男性的色彩。
看理想:近几年,许多中国女性认识到了传统的婚姻模式对女性的压榨,因此拒绝婚姻。但是,部分选择不婚的女性对已婚已育的女性抱有敌意,用“婚驴”这种侮辱性的词语来形容她们,认为她们是父权制的帮凶,即便遭遇不幸也是自作自受。
在日本,不婚和已婚两个女性群体之间,是否存在这种对立?您如何看待这种对立?
铃木凉美:先看统计数据。在过去的50年里,日本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上升了5岁左右,但最近一直处于高居不下的状态,没有显著的变化。50岁未婚率(原来叫“终身未婚率”)则是持续缓慢上升,东京约为20%。低收入群体在未婚男性中占比较高,女性却表现出了收入越高,未婚率就越高的倾向。
放眼周围,不走入婚姻,任年岁增长的女性确实不少。被蔑称为“剩女”、亲戚讳莫如深之类的事情也少了。但将视线转向年轻群体,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结婚意愿反而相当高,几乎看不到避讳婚姻的观点。年轻网红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例子也很多见。
此外,政府在今年4月对法律进行了修订,将男女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统一成了18岁,成年年龄则从20岁下调到了18岁。年满18岁后,无需征得父母同意就可以结婚。
据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女权主义者对婚姻相对不那么消极,批判全职主妇的言论也仅限于一小撮人。因此和问题里提到的中国的情况相比,日本的婚姻肯定派与否定派的对立要相对温和一些。
虽然我大体上认为,否定派和肯定派“相互认可”比“因为分裂变得咄咄逼人”要好,但日本的这种倾向是有大背景的——男女的薪酬差距仍然很大,不结婚会带来生活层面的具体不便(社会信誉低、无法接受辅助生育治疗等等),再加上单亲妈妈往往深陷贫困,便形成了“不肯定婚姻就活不下去”的社会环境。
换句话说,日本的现状称不上“婚姻肯定派与否定派在公平的条件下实现了互相认可”。
看理想:书中您和上野千鹤子教授讨论了年轻一代女性,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但又因为什么都想要而迷茫无措的状态(“她们身披浪漫爱意识形态的余香,带着男权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的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奔西走,手足无措。”)。
这似乎是过渡一代女性的宿命,在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对于这种迷茫状态,您是否有什么建议?
铃木凉美:通过学习变得更聪明的女性应该都会直面这样的苦恼:“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和“心底真实的欲望指向的选择”并不一致。
在我看来,原因之一可能是过渡期女性在儿时接触到的文化、在大学里学到的思想和此刻展现在她眼前的现实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好比1992年(我9岁的时候)制作的美国迪士尼电影《阿拉丁》和2019年(我36岁的时候)上映的真人版《阿拉丁》,两部电影的女主角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童年时梦想的幸福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相当根深蒂固。要是再牵扯到不能自控的恋爱元素,知识和真心话就有可能进一步背离。你可能会被聪明的自己理应否定的错误言论深深打动,也可能在学到的知识的作用下,在与伴侣的恋爱中踩下刹车。
尽管矛盾与纠结是痛苦的,但我完全不认为那是坏事。因为内心时刻被两个以上的选择撕扯,至少意味着你没有盲目相信某个判断标准是绝对的。
我们也可以说,以前的时代之所以看起来更简单,是因为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不过是“无限种可能性之一”的看法,在当年被洗脑成了“绝对的唯一”。
希望大家不要畏惧矛盾,想做就尽管去做。
没有人能在方方面面贯彻如一,所以哪怕跟自己平时的主张不一致,也应该伸手去拿真正想要的东西。即使结果是一样的,毫不犹豫拿下的东西和在纠结撕扯中得到的东西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我有一种预感,这个烦恼纠结的过程会使女性的未来变得更自由、更精彩。
看理想:中国在近两年出现了一个说法,“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看透男性的本质后,仍然爱他们”,以此来表达顺性别异性恋女性面对的苦恼。
您在书中也有相关表述,包括与外国男性而非日本男性交往。但上野千鹤子老师认为,“恋爱是谈了比不谈好”,因为能够帮助我们确认自我,“我要成为‘女人’,就需要‘男人’作为恋爱游戏的对手”。在与上野千鹤子老师对谈之后,您对于恋爱的看法有改观吗?
铃木凉美:恋爱观和男性观是我在此次通信后产生很大变化的部分之一。我一度通过对恋爱摆出嘲讽的态度,在自己和周围的男性之间筑起高墙。这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对男性绝望,还因为过去的工作经历促使我设置了心理防线,以免受到伤害。
但上野千鹤子女士的那句“我无意说‘反正男人已经无药可救了’”,以及指出“恋爱是谈了比不谈好”的那封信,让我渐渐想在男性身上找到值得相信的东西了。转变想法的过程,也是我再次面对过往的过程,这对我来说是很不舒服的,也伴随着痛苦。
这本书在日本也才刚出版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我被关系亲近的男性直接伤害过,也被过去的自己间接伤害过,但和疏远男性、认定“相信他们也是白费力气”的时候相比,我似乎品尝到了更多的解脱感。
03.
或许关于将来
看理想: 您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有喜欢的作家吗?为什么?
铃木凉美:在日本的作家里,我一直都很喜欢金井美惠子女士。她既是小说家,又是评论家和女权主义者,我很向往她那不趋炎附势的观点和不惧怕孤立的写作风格。如今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年轻时的文字,感觉受她的影响很大,或者说,当年的我大概很想成为她那样的人吧。
上世纪70年代还有一位叫铃木泉(鈴木いづみ)的作家。她是1986年去世的,当过陪酒女和裸体模特,演过桃色电影(译者注:含有情色或软式色情成份的日本成人电影),年轻时就以小说家的身份出道了,留下了许多作品,包括科幻作品和电影散文。
她的外型是个十足的性感风尘女,但在阅读她的科幻作品和其他作品时,我觉得她是在用一种独特的性别观审视社会。而且她的经历与我有相似之处,所以我对她有着别样的感情。
在外国文学方面,我最近又读起了学生时代很喜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本,人们不太有机会就信仰开展思考,但他的小说是我对宗教和信仰感兴趣的契机之一。
除此之外,我也经常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如《爱丽丝梦游仙境》《毛毛》,和南美文学,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罗贝托·波拉尼奥。
看理想:从书中能察觉到您对父权社会以及男性都非常失望,甚至认为沟通是徒劳,那么,您现在所做的研究、写作以及公共表达,您认为能够改变一些什么吗?您的写作是否是一种面向女性的写作?写作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铃木凉美:与其说我是对社会和男人深感失望,不如说我是早早死了心,认定“不会变的永远都不会变,说不通的永远都说不通”。比起“拼命去改变不会变的东西”,我对“如何在一个不会改变的社会中活得舒心快乐”更感兴趣。
通过描写我摸索“如何在这个严酷的世界快乐地活着”的过程,呼吁广大女性“想办法在这个世界舒舒服服活下去吧”——我写的东西好像基本都有这样的意图。
早在年轻的时候,我就想轻快地活着,不站在想要改变的一方,也不站在抗拒和阻碍改变的一方,这种感觉至今仍多少伴随着我。
然而从结果看,这样的态度无异于补足和支持拒绝变革、阻碍变革、旧态依然的社会,这也教人不爽,所以我最近也觉得,在不方便但也不是住不下去的屋子里找一处舒适的地方,也许还不如干脆舍弃或推倒那令人不适的屋子。
由此可见,我自己也很矛盾,但我相信在这样一个社会全力打拼的同龄女性朋友肯定也面临同样的两难。她们想改变现状,但又不会默默等待事态转变。所以我想写一些她们愿意看的、看着有意思的东西。
看理想:您在书里多次提到自己的写作被误解和消费所带来的困扰,您现在如何看待这种困扰?它们影响你的表达了吗?
铃木凉美:AV女演员往往有这样一种倾向:一旦有人在片场提要求,她们就会下意识扮演“听话的乖宝宝”,尽可能满足对方的期望,即使这意味着勉强自己。我也不例外。正是因为这种倾向,我原来确实经常遭到带有恶意的或性色彩过重的消费。
最近,这种违背我本意的消费有所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在喜欢小姑娘的日本男性眼里,我已经渐渐淡出了性消费对象的范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自身的想法有所转变,觉得“因为背叛了那种期望和消费惹人嫌了也无所谓”。
随着这种消费的减少,我写的东西被那些拥护色情产业、对表达自由持极端观点的人曲解利用的情况也变少了。
我的心境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每天都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不让神经变得迟钝,也许就没法应付过去。最近这种情况出现得少了,于是我听从心声发火或反驳的情况相应增加了。
通过抗议,我也可以反思自己的哪种态度引发了那样的消费,稍微费点心思采取预防措施(哪怕只是提前加一句“我不是~的意思”),也就不容易被断章取义了。归根到底,还是只能脚踏实地地用语言去表达在每一个误解和每一次违背初衷的消费中感到的“不对劲”。
看理想:您有什么对中国读者特别好奇的问题吗?或者有什么想对中国读者说的吗?
铃木凉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世界第一的人口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而在我的印象中,特别是在女性赋能这方面,中国自70年代以来一直走在东亚地区的最前列。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法国还高,女性官员也多。中国女性有时比男性更有上进心,不太有“靠男人”的观念。
这些都是我通过媒体报道勾勒出的中国女性形象。还有中国本土的时尚品牌、导演、作家……中国女性在世界舞台上的活跃让同样身为亚洲女性的我深受触动。
起初我都有点纳闷,不明白在一个女性如此强大的国家,大家为什么会对在日本这样一个女性赋能后进国开展的讨论产生兴趣。
不过跟住在日本的中国朋友和现居上海的大学好友聊过之后,我发现中国的女性虽然能享受到优越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但仍有一些女性在养育子女和自我实现之间苦恼挣扎,或是被性骚扰和男性贬低女性的态度所伤害。在这些方面,两国女性似乎也有许多共通的烦恼。
作为一个与“虽然取得了成功却感觉缺点什么”“接受的教育和学到的思想与自己的欢愉并不一致”这样的困境作斗争的女性,如果我能向有着类似烦恼的邻国女性朋友抛出些许想法、共鸣点或有助于治愈的观点,那就再好不过了。
看理想:您希望留给妹妹们一个怎样的世界?
铃木凉美:虽然经历过风风雨雨,但我大体上很享受、很中意自己的人生。即便如此,我有时还是会因为扎心的话语夜不能寐。
无论置身于多么理想的社会,只要一个人还有智慧和感性,就必然会产生不安、焦虑和烦恼。但我还是希望,妹妹们能活在一个不会被人搞得心烦意闷、辗转反侧的世界里,每年能比我少熬那样一个夜晚都好。
协助:新经典
采访:猫爷、Purple、林蓝、汁儿、苏小七
编辑:林蓝
监制:猫爷
配图:《问题餐厅》《初恋的恶魔》
《小偷家族》《直美与加奈子》
《迈向未来的倒数10秒》《有点心机又如何》
封面图:《你的鸟儿会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