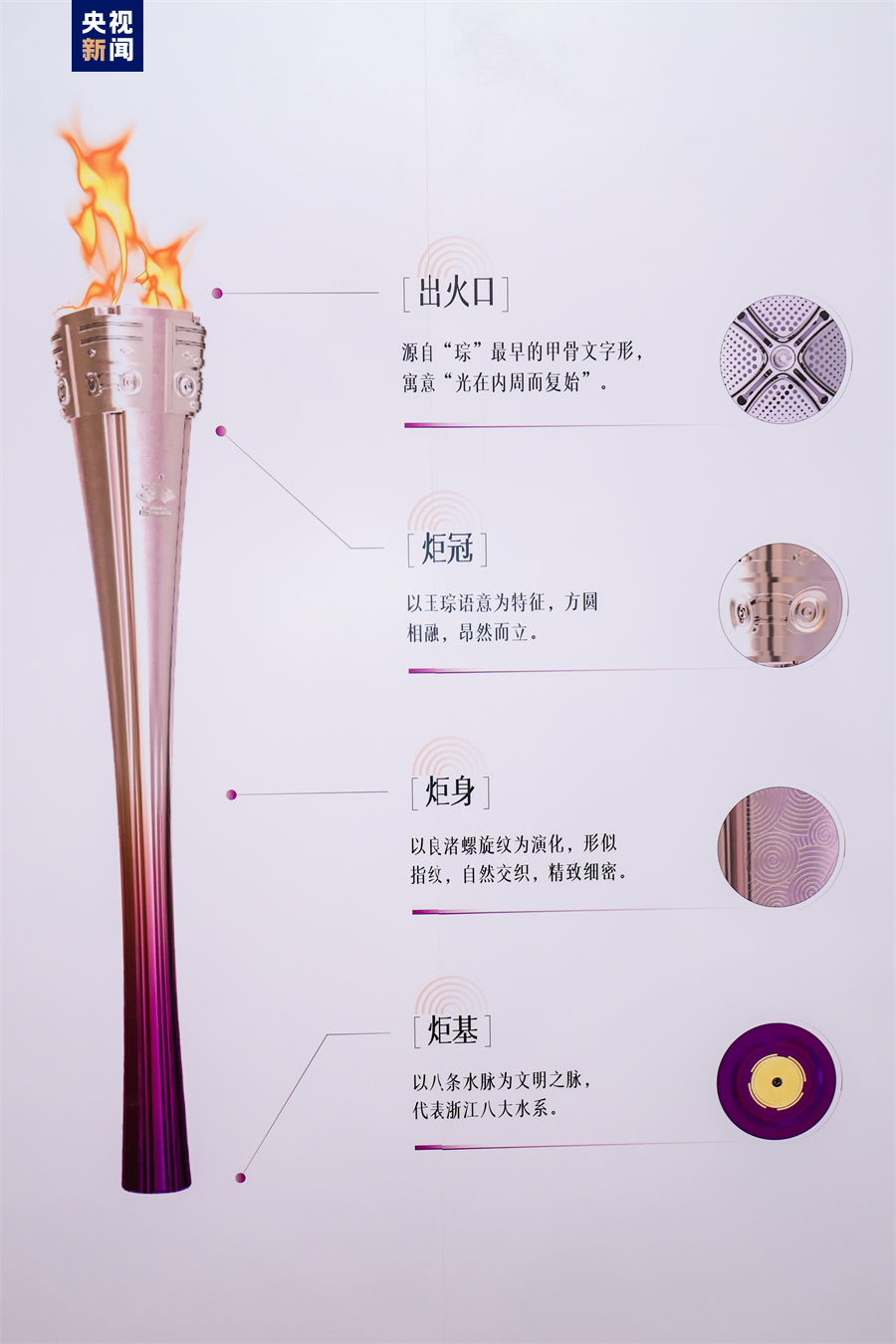捡秋别变成了“偷”和“抢”
资料配图,与文无关,视觉中国供图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作者 | 李 强
编辑 | 杨 杰
在北方,寒露一过,正是收大豆的好时节。秋收时分,等他人收完地里的庄稼,再去捡少量漏掉的,这种行为被称为“捡秋”。可是最近,一群捡秋的人惹得河北一位土地承包户很恼火,在大豆地里怒吼着驱赶。
原本,捡秋是要获得土地承包者的允许。然而一些不自觉的人,没打招呼,就往自己麻袋里捡。华北平原上,豆子熟了,收割机来了,捡大豆的人也来了,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有的是捡,有的成了“抢”和“偷”。
被疯狂捡拾的不只是大豆,还有花生、玉米、稻谷、土豆。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去年、前年都出现了类似的“捡秋大军”。每当秋收到来时,这些人齐刷刷过境,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自顾自地捡粮食。这让一些土地承包户极其头疼。
在河南某地,当收割机一排排收玉米时,捡秋的人就立在一旁,蓄势待发,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麻袋和镰刀。收割机过后,没等种植户自己去捡,就三下五除二地抢完了遗落在地上的苞米,有时甚至逼停收割机,农户不得不出于安全考虑在一旁呼喊:“不要围得太近”,只是并不管用。据说,在一些地方,发生过捡秋的人受伤,甚至被卷进收割机而死的事。
如果是夜里,捡秋的人会开着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赶来地边,机器收割时,他们则戴着头灯在地里捡,仿佛办了一场有关丰收的灯光秀。但承包户高兴不起来,心里装着无奈。捡秋的人多是附近村庄的老人,吼也吼不走,拦也拦不住,有时还要叫来村干部、警察维持秩序。
对农民来说,这是一年收成的好季节,对一些捡秋的人来说,这变成了一年一度“薅羊毛”的好时候。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一些尚未被机器收割的玉米,也会被掰走。有的悄默默趁人不注意,有的则当着承包户的面,大胆地从玉米秆上掰下来。承包户迫不得已开车驱赶,但人单力薄时,没办法应付上百人的哄抢,也有农户愤怒地将被捡走的土豆从陌生人的筐里倾倒出来,可是又被人从地上捡了回去。
有承包户不得不大声疾呼:“乡亲们啊,种地不容易啊,手下要留情啊!”但那些人无动于衷。
捡秋,本来是一件稀松平常、芝麻大点儿的事,是庄稼人珍惜粮食的一种表现。我小时候也捡过秋,自家田里的稻子割完后,就弯腰四处搜寻遗落的稻穗。等自家捡完,附近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来捡。那些老人总能从边边角角的地方,捡到好些稻穗,捆扎成把,带回家晒干碾米。那会儿,谁也不会在乎有人捡走三五把稻穗,也没人脸皮厚到哄抢他人的庄稼。
原本,捡秋的规矩是约定俗成的,尽管它本质上是一种“占便宜”的行为,但农户不会无奈、愤怒,也不会对捡秋的人有什么怨言。捡秋的人对脚下的田地怀着敬畏,对田地的主人有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今“捡秋大军”的行为,多少有些 “吃大户”“薅羊毛”的味道。捡秋的边界一点点被打破了,从未经许可就迈进他人地里的第一只脚开始,从偷偷掰掉未收的玉米的第一只手开始,从那一点儿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的消失开始。
也许在一些捡秋者看来,承包户、村干部、警察是管不过来的,法不责众,更不责老。不捡白不捡,白捡谁不捡。于是,“捡秋大军”的胆子越来越大,手越伸越多,越伸越快,越伸越长,捡就变成了偷,甚至是抢。
今年8月,武汉新洲一位95后姑娘种的南瓜就被偷了。她承包了1000余亩土地,南瓜成熟时,附近的村民骑着电车、拖着板车、拿着麻袋频繁到她的地里偷瓜,被她抓到后,有的坐地不起,声称自己上了年纪,身体有病。她报了警,警方只是口头教育。后来,她的瓜被人报复性地砍了。
这样的事,往小了说,不过是捡了几粒米、摘了几颗豆、拿了几个瓜,可说大了也要牵扯上法律与道德。只是从法律上看,偷抢粮食要足够多,才够得上盗窃罪;或者两年内三次偷盗,才够算被认定为“多次盗窃”。
法律是拿来兜底的,捡秋时的小偷小摸行为,常常因涉案金额少而难被认定为“盗窃罪”,就算咬牙切齿地叫来警察,警察也顶多批评几句。更多时候要靠道德约束人心小小的贪欲,但有些时候、有些人总是“以恶小而为之”。
前些天,我也碰上了类似的事情。国庆后,我在河南老家多待了一段时间。一天傍晚,我跟母亲去村西边自家坡地摘茶籽,准备留作茶种,若有多余的就拿来榨油。等到茶叶地里却发现,两位陌生的女性正偷采茶籽,母亲很生气,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有人偷茶籽。
其实被偷的不止茶籽,村子里的板栗也被不少村外人偷。板栗成熟时,不少陌生人都会骑着摩托车,甚至开车来偷板栗,其中不乏县城的人。母亲说,这种情况已不是一年两年了,即便抓住也只能撵走,但过两天乘人不备他们又来了。
他们往往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偷”,借口是“我以为你不要了”。仿佛这样一句话,未经允许的采摘就变得合理合法。没人告诉过那两位陌生女人,茶籽和板栗不要了。相反,她们的目的是明确的,工具是专业的。她们在一位亲戚的带领下,从县城开着汽车来,那位亲戚正是我们邻村的人,知道这片茶叶地的位置,并准备了手套、麻袋、水、遮阳帽和口罩。
我和母亲到时,她们已经摘了两麻袋茶籽。我很生气,毫不客气地对她们说“一颗也不能带走”。晚上,父亲接到那位邻村人的丈夫的电话,那人在电话里说我讲话很凶,“跟吼贼似的”。我心想,未经允许,这不就是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