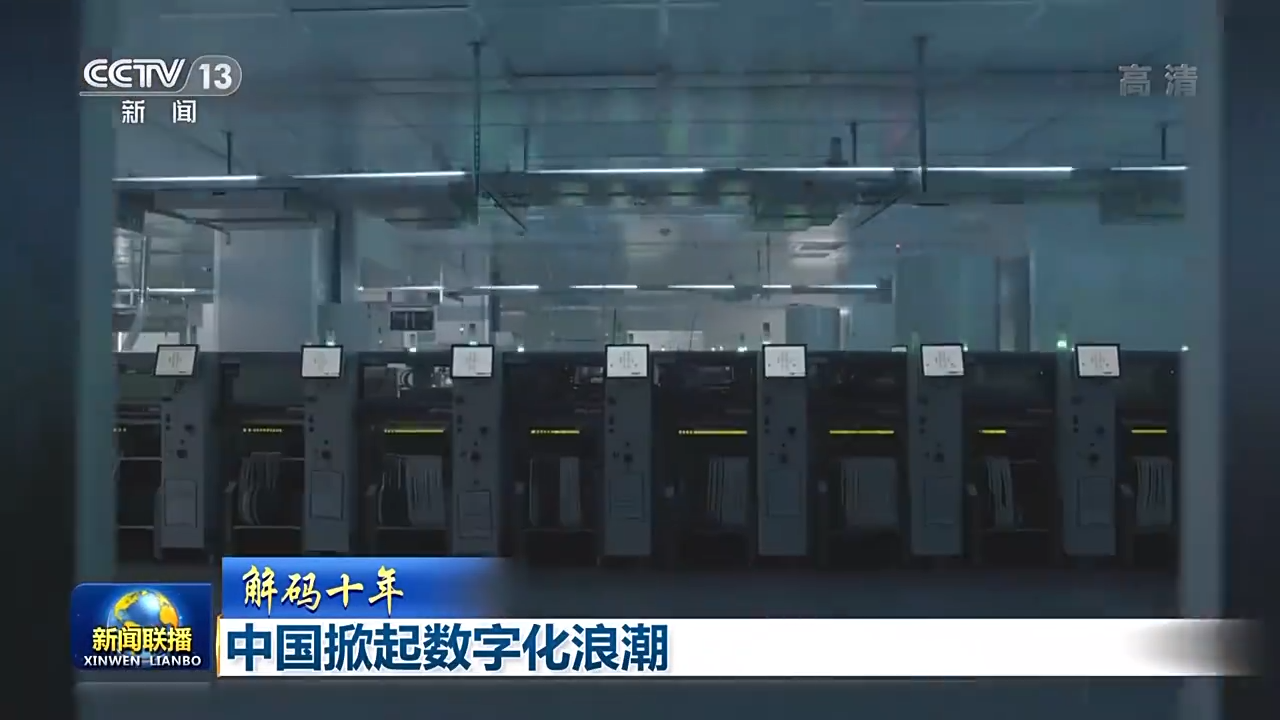理科状元的记者梦:曾因想学新闻被记者苦劝引关注

很少人会有吴呈杰那样的经历:刚捧着梦想跨出第一步,就被当头泼了一壶冰水。
他至今记得那个时刻。2014年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个晚上,这位新晋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被带到校长办公室接受采访。当现场七八个记者听到他“想当一个新闻人”的志向之后,采访的气氛变得不同寻常。累,薪水低,报道常常受限……开始是一两个人讲述职业辛劳,最后大家伙七嘴八舌在吴呈杰面前“开了个吐槽会”,“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报新闻”。
此前一直在寄宿制中学埋头读书的少年感觉“心一下就沉了”。
没过几天,“江苏高考理科状元想学新闻被多位记者苦苦相劝”的消息就炸了锅。一位高中老师带着“恭喜”的语气提醒吴呈杰:你上了微博热搜榜。而当他闻讯打开网页,除了见到与自己有关的新闻与女星Angelababy(杨颖)一前一后挂在热搜榜上,还不停收到网友的“问候”:一种劝他千万别学新闻,另一种骂他背弃理想。
如今,读经济专业的吴呈杰是北京大学一名校媒记者,这个自认“路痴”、“害羞”的“小镇青年”对未来的打算是——做新闻。
作出“努力去当记者”的决定之后,他给远在老家的父母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在30岁前就不考虑结婚了,因为养家糊口可能会有困难。
虽然才读大二,他已经“听熟了当记者的坏处”,大概总结一下,“无非是收入少,有限制,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他觉得都还可以。吴呈杰目前就读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该学院的毕业生薪酬全国最高,但他觉得,对金钱“没啥感觉”。
让这个理科生有感觉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13岁时,在乡村中学读书的吴呈杰看到了《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感觉“热泪盈眶”。
他自觉是个“非主流理科生”,从小就喜欢文科。小时候在学校里因为浓重的乡下口音受排斥,他就把精力放到了读书上。去年夏天成了“理科状元”之后,有网友在微博访谈中提问:“学霸,高中时期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学霸”的回答是:几本反复读的书——《百年孤独》、《瓦尔登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路上》。
高三的寒假,他征得父母同意,还跑到上海参加了一回新概念作文大赛。而那次帮助他入围决赛的报名作品,是他在一次物理竞赛的赛场上写的。这篇小说后来被刊登在《萌芽》杂志上。作文竞赛,他也得了一等奖。
但进入北大的“状元”们,大多会报读光华管理学院——全国最好的商学院。
吴呈杰的师兄,北京大学中文系2013级本科生谢宇程阳还记得,因为主编着学生会一本校媒刊物,去年新生入学时,他就特别想招这个新人。但他们去“刷楼”,以学生会宣传部的名义招新,等全部面试都结束了,也没等着吴呈杰的人影。
直到谢宇程阳给新人做完了采写培训,才收到吴呈杰的微信好友申请:我想加入宣传部。
吸引他的是宣传部部训时提供的一本长篇新闻报道范文集。
不久之后,谢宇程阳见到了一条让他“一瞬间非常感慨”的朋友圈:“三个人六目相对想了整整三个小时,只为确定5个小标题”。
吴呈杰就是那三个人之一。他被谢宇程阳描述为“可爱、实诚、憨厚”,在另一位学新闻的同学眼中最大的特点则是“每天琢磨的事都是新闻”;这个在小升初的时候因为太害羞而没能通过重点中学面试的96年生人,如今常常会花上一两个月去做一篇报道,不断跟陌生人聊天。
尽管如此,直到几个月前,他才真正下决心要朝着新闻行业发展。
他说自己想到了高中文理分科的时候——他的文科理科成绩都好,长辈告诉他,如果选理科,以后就业面会更广。
“但只有我自己明白:理科学得好,是因为我下工夫,文科学得好,是因为我有天赋。”
到了大学里再回望往事,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一步步都走得“太正统”了?
他最终成了一省的理科状元,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新闻报道中找到了最大的“成功感”。
他去采写了校园一些边缘群体的报道,报道阅读量突破了10万。北大的流浪猫不幸去世,他不满足于像“官方色彩浓厚”的校媒那样写点“号召保护小动物”的报道,反倒想探究动物保护的困局,结果被流浪猫保护协会的采访对象给赶了出去。
他与同学一块儿尝试过许多选题:北大的学生诗人,工人诗人,大学里的基督教群体……然而每每因为题材“太超前”而被老师的劝阻。
他发现学校更偏爱报道师生中的好人好事。这让吴呈杰感到有点忧心:很多不那么好听的报道与学生利益更有关系,我们的报道是为了学校好。
当谢宇程阳离开校媒的时候,他把主编的职位交给了吴呈杰。
“北大有很多同学都有非常好的家庭背景,一路走来非常顺畅,而吴呈杰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在我看来,他双脚虽然沾着泥土,从外表上来看略显稚嫩,但他的脚步是坚实的。”
大众印象里有一个“因为‘良心记者’劝说而放弃了新闻学的高考状元”;很少有人注意到,在2014年夏天的喧嚣过后,还没上大学的吴呈杰在微博上转发了一段话:新闻是一条注定要长跑的路,一朝一夕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要相信新闻依然有助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你会是千万推动者中的一员。在中国新闻的历史中,有千千万万名记者奔跑在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
“我也许当两年记者就熬不下去了呢?”现在谈起未来,这个19岁的青年也并不肯定,但很快又自言自语:“应该不会吧?只要饿不死,我都会写下去的。”(本报记者 黄昉苨)